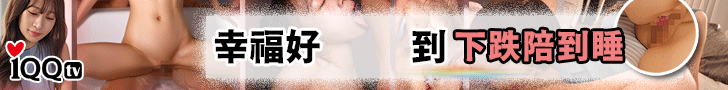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1)
水白初到G城的时候,是单身一人。两年了,水白再不能说自己是单身一人了。有时候看见了G城污糟无比的廉江里竟然也游著活鱼,感觉真是遇到了老乡一般的舒畅。同类是到处都有的,只是经常地缺少能发现的眼睛。
人是容易寂寞的,谁也不能怀疑这一点。即使与人类不同群落的猫狗之类也是如此。猫叫春是最为凄惨的,听起来绝对不像是一只猫对另一只猫呼喊说:“亲爱的某某猫,我们来做做爱吧。”
水白听到猫叫春会很尴尬,在路上碰到了两只狗交尾也是会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半边。感觉是自己的同胞姐妹那么不顾廉耻。倘若有人能够一把摀住猫的嘴,或者把自己家的棉被抱出来把交媾的狗遮住,水白就算是根本不爱这个人,她也愿意嫁给她或他,或者他或她随便开口要自己的那一段年华献给她或他也是可以的。
寂寞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个人,这个跟猫狗之类也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猫吃饱喝足不寂寞自己玩耍的时候,水白想她肯定不会想到别的猫的。她那么慵懒地躺着,眼睛即使四处瞅著,其实终究是看着自己,她只满足于自己的样子,周围的一切不过是细枝末节的东西,是用不着她费心费神的。
水白也是懂得寂寞的,只是寂寞的程度自然比不上叫春的猫。经年累积的好朋友都不在一个城市,就算是打打电话,各自都在不同的时空,要真正沟通还得自己把自己翻译一遍,对方才能听懂。
水白经常做的一项运动是爬山。G城恰好是山水之城,虽然也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才能爬上一座山,但也总比走一个小时的路去见一个人好。
山不是很高,但是绵延著也有很多山坡,要爬完所有的山坡再掉回原路也要花上几个小时。周末的时候,爬山的人特别多,山上还有公园,让人消遣或做其他运动。水白就光自己一个人爬,上山下山的人也多,所以对于人身安全之类的问题也没多想过。
但有一会就差点出事了。那时水白坐在半山的亭子里,自然也有陆陆续续的人经过。水白靠着柱子闭着眼睛休息,突然就有水从头上倒下来,灌了水白一头一脸。
水白睁眼看,竟是一个小女孩,十二三岁的样子,手里拿着一个空的矿泉瓶。水白本来是可以发火的,不过刚好正出汗,这淋在自己身上的水倒也清凉无比。
小女孩目呆呆的,也看不出灌了一通水白之后的任何快感或者调皮。水白真是想不明白这个小女孩为什么非要浇她一头水。
水白问小女孩:“你也是一个人么?你的爸妈呢?”
小女孩只是警惕地看着水白,并不说话,感觉不是水白而是她被外人侵犯了一样。
水白再问:“你在读初中吧,你穿的是校服?”
小女孩还是不说话,不过僵持了一会,突然就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子往水白身上扔,然后掉头就跑。
水白一时来了兴趣,也跟在小女孩身后跑。小女孩看见水白跟着,不停地发出尖叫,直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呵斥:“艾子,你又在作弄姐姐了。”
是一个女人,站在比水白高几级的台阶上,手叉著腰,看看那个小女孩,也看看水白。水白站在那倒有点不好意思,说:“你的孩子有点调皮。”
那女人说:“不好意思,大概打搅你了,艾子就喜欢自己捣鼓著玩,请你别介意。”
水白说:“没事,我小时候也是如此。”
那艾子本来都跑到前面的台阶上了的,这回又下得台阶来,来挑逗水白,然后又尖叫着跑,水白也满足她,跟着她跑。
水白跑了一会,突然腿抽筋了,一时疼得坐在地上咬牙。艾子的母亲看到水白突然就坐在地上,很快跑过来,问水白怎么啦。水白告诉她说:“老毛病,腿抽筋了。”艾子的母亲说:“我给你按摩脚底,好的快些。”水白不好意思,不过那女人自顾自脱了水白的鞋,隔着袜子就开始给水白按摩。
艾子也跑过来了,很认真地看母亲按摩。那女人说:“你的脚真是柔软,我从来没有碰到这么柔软的脚。”
水白笑笑说:“我自己没感觉。走路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的脚软。你是按摩师?”
那女人说:“不是,不过我喜欢给人按摩。我按摩很舒服吧?”说完她看着水白笑。
水白说:“是挺舒服的。”不过她看见了那女人看自己的眼神,心里突然就不舒服了。那种眼神怪怪的,好像有点要作恶的意思。
(2)
水白不愿意再看到那样的眼神,就自己闭上眼睛。那女人的手也是柔软,不过也可能是陌生的手的缘故,反正就是觉得好,连体温都带着可爱。
水白正想着如何跟这个女人搭讪下去,不搭讪是肯定不行的,人家这么好心地免费为自己服务。突然那女人一阵挠水白的脚心,水白忍不住一顿好笑,拚命想缩回自己的脚,无奈被那女人抱得死紧。
水白真是没想到竟然有这样作弄人的,但也发作不起来的。那女人挠一会儿水白的脚心,自己也笑一阵,看着水白,眼睛里还是那样作恶的宣示。艾子也在一边咯咯笑个不停。
水白自己不能忍禁地笑,但慢慢笑得就有点要哭的意思了,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求饶。不断地重复说:“天,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但越求饶,那女人竟然挠得越有技巧,水白就越是痒的整个人除了笑不知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摆脱那样的痒意。
那女人笑着说:“快叫我宝贝,不然我不停。”
水白倒是闷了,这也太离谱了,自己可是从来没叫过人宝贝的,就是小孩子也没叫过的。何况还是一个陌生人,怎么叫得出口。
水白还是难受得不行地笑着,真是没法叫。奈何不得就用手去掰那女人挠著的手,可是自己的力气明显敌不过她。
那女人一边挠一边还说:“快叫,快叫我宝贝。”
旁边经过的人看着她们这三个大小的女人如此可爱的亲密方式,也都觉得好笑,停下来看一会,笑着继续走路。
水白心里想恨竟然也恨不起来。
这身体实在是痒得不行,可是笑得也是非常放肆的。水白感觉自己两年来都没这么大声笑过了,竟然还是高兴的,真是奇怪。
可是不管什么,身体的感觉毕竟是身体的感觉,痒酥酥地还是难受,这样下去会笑死人的,尽管笑着听起来很开心。也是被自己的笑感染了,所以心里才会觉得开心。
水白决定还是妥协的好,好不容易挤出两个字:“宝贝”,自己已经不好意思看那女人了。那女人还不罢手,说:“不行,声音太小。”
水白只好硬著头皮用大一点的声音说:“宝贝。”说著的时候眼睛是看着树木的,好让自己能坦然些。
那女人说:“你得看着我的眼睛叫,叫我青青,再叫宝贝。”
水白一听,脸又大大地红翻了一次。心想:“宝贝已经够腻味了,还要亲亲。这女人真是够让人折腾的。不过叫就叫,也就是让自己装得木然一些就是。”
水白看着那女人的眼睛,努力要让自己不深入地看,只是假装着看。那女人的眼睛倒也显得平常,没什么深意的,可是越平常,水白反而越是不能平常地对着她的眼睛。
水白只好笑着躲藏着她的眼睛尽量温柔地说:“宝贝,亲亲。”
那女人呵呵笑说:“叫得真是怪腻的,不是亲亲,是青青,我的名字。”
水白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那里管得了那么多,反正任务算是完成了。那女人也终于放了手。
(3)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水白倒觉得跟青青一下亲近了好多。脸都红过了,最难堪的境况也都被人家看了去,似乎也没什么秘密可以相瞒。如此水白便开始慢慢放松自己。
青青是那种很讲究很精致的女人,衣着自然是光鲜的,皮肤也是保养得很好,不仅白净,而且脸颊还保持着少女的红晕。水白看着她想,大概这女人每天除了把自己的形象维护好,也不会做别的事。漂亮是漂亮,可是这漂亮付出的代价也是够大的。水白自己是不甚讲究外在衣着和美容,反正每天出门前在镜子面前一站,自己感觉满意就行了。涂涂抹抹的年龄似乎已经过去了,工作的繁忙足以把一切繁文缛节、小资情调和搔首弄姿都省略掉。
活的脚踏实地大概也就是如此。况且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也正处于资本积累时期,离后现代的无聊空虚无所事事地自我分裂还远着呢。
不过青青说:“资本积累,对于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理财。”
水白说:“我每个月挣的工资还不够我自己花,我理什么财啊?”
青青说:“这就是你年轻不懂了。你每个月的工资不是财啊?有财就要学着让它增值。增值不一定是你今天五块钱,明天就变成十块钱了。关键是要懂得投资,让你投资的东西增值,这比让钱直接生钱容易多了。比如现在正是经济萧条期,倘若你直接把钱花在做买卖上,能不亏就不错了。”
水白说:“我不明白我有什么可以投资的,也没有生意头脑。”
青青说:“我们女人看东西最好不要看硬件,比如自己开公司,拥有多少资产之类,这些硬件都是身外之物,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应该看软件,那些属于自己的品格和素质,这些东西你只要活着,一辈子都还是你的。”
水白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青青说:“明白是明白,做是另一回事。我就没见过有多少女人做得很好的。”
水白想,大概青青自己以为自己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青青说:“比如现在的经济萧条期,女人至少可以做两项绝对不会亏本的投资。一是美容健身。别以为男人甚至女人说了真的不会在意你的容貌,就真的不在意。即使在爱着的时候也是如此,没有不适应美丽的眼睛,只有不适应丑陋的眼睛。外在形象的美好绝对是一个女人的不动产。我就想像不出世间有那个人忍心让一个美人饿死。等经济复苏了,甚至就算是经济萧条期,美人都是供不应求的。”
水白是很反对把一个人当作物品来评估价值,不过即使拿别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其实本质还是一样,还是把人当成了物或者可以评估的对象。青青说的也是事实,水白不好反驳。
青青接着说:“除了美容健身,第二项可投资的是教育。这对于那些不屑于以容貌取悦于人的女子是很好的增值法子。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期,万物待新,正好可以拿出点闲钱给自己度度金,就算不是为了谋生,也能增强自身的修养和品味。你别小看修养和品味,不管你有钱没钱,都能使一个人显得高贵。”
在水白看来,所谓的修养和品味其实就是让一个人越来越脱离动物的低级趣味,越来越有人情味。说白了,也就是让一只寂寞的猫的叫春装饰得异常浪漫和美丽。
水白陪着青青和艾子爬完一座山坡就下了山。路上也主要是青青在说,水白基本就是附和了。不过也许是青青太女人了,水白觉得也有一种可爱。下了山,也就分头各自回各自的住所,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人与人的相遇就像水流流过石头。
(4)
水白上了公交车,想掏出手机来看看时间,摸摸口袋才想起手机放青青包里忘了取回。水白赶忙下了公交车,往回走,心想青青说不定还在山门口。
一阵火急火燎地赶到山门口,果然看见青青和艾子坐在敞棚的饮料店喝水。青青远远地就朝水白喊:“我就知道你肯定还会回来找我的。”
水白说:“不好意思,我手机忘你袋子里了。”
青青倒奇怪了:“手机,你是回来取手机的啊?我倒也忘了。”说完就从挎包里摸索半天把水白的手机拿了出来。
水白问:“你刚才说什么我肯定会回来找你?”
青青说:“没什么,是我自己的感觉。感觉着你走得不踏实。”说完就朝水白很有深意地笑笑。
水白也是个敏感之人,听她这么一说,差不多又要脸红了。
青青说:“不如你记下我的电话吧,万一你又忘什么在我这。”
水白说:“我那有那么多东西忘你这啊。”说归说,还是很认真地把青青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输进了自己的手机。
水白低头输电话号码的时候,心里嘀咕,感觉著自己这么认真地记下电话号码其实是做给青青看的,以补偿她那深意的笑。
青青又说:“你是每个周末都来爬山么?”
水白说:“差不多是如此,除非下雨或者有别的事情。”
青青说:“我前天晚上做了个梦,说不定你能解呢?”
水白说:“我又不了解你和你的生活,恐怕解不了了你的梦。”
青青说:“我感觉这个梦好像跟你有关似的,你听听好了,解不解无所谓。”
青青的梦是这样的:
青青一个人来爬山,没有艾子。路边有一棵树引起了青青的注意,青青觉得这棵树好像跟她有什么关系似的。果然那棵树说话了:“我有一样东西忘你家里了,你没给我带来么?”青青说:“没有,下次我一定给你带来。”青青在梦里觉得是有什么东西该带却没有带来给树,但那东西是什么,印象很模糊,好像是块美玉什么的。
一会又梦见在海边,青青和一个陌生的女子一起用沙子做一个小孩,两个人配合很默契,没多大功夫就把小孩给做好了,小孩还很漂亮,两个人都很高兴。青青在梦里感觉自己是单身,没有小孩,而那个陌生的女子也是单身。
水白说:“你这个梦确实大有深意,不过不一定跟我有关。想听我解释给你听么?”青青没想到水白还真能解梦,高兴地直催她快解。
水白说:“你很快将会跟一个女子发生一段情缘,或者你渴望发生一段情缘。这段情缘的发生,你是主动也是关键的一方。那棵树和海边的那个陌生女子是同一的,美玉和漂亮孩子象征爱情。但这份爱情虽然看起来很美,却不会很牢固。”
青青听水白这么解释,好像不是很高兴,说:“这么个破梦,你说得倒是有鼻子有眼的。”
水白笑笑,没说什么。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如此不堪自己看破。
(5)
生活可以是美味的,每个日子都像一桌菜摆在自己面前,客观地说没有做得不好的菜,只有吃的人胃口好不好,反正水白是这样想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即使糟糕透顶的事情,水白也能在沮丧之余,找到可享受的一面。
每天还是照常上班下班,太阳偏东也好,偏西也好,人还是一样的过下去。有时候水白怀疑自己是可以长命百岁的,每天这样的过活,感觉日子似乎无限漫长。
一日无聊,水白翻开电话本要给一个老朋友打电话。那边电话接起来了,却不是老朋友的声音,水白就说了老朋友的名字,问在不在。电话那边的女人噗哧一声笑了,说:“水白,你竟听不出我的声音?”很有责怪的意思。
水白愣半天,感觉声音是很熟悉,可就是想不起是哪个人。那边那声音又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会等你电话么?”水白支吾著,模模糊糊说:“我这不就给你打么?”那边那声音说:“你还有一样东西在我这呢?你要不要拿回去?”
说到这水白才明白过来,对方是青青。可是也奇怪,明明拨的是老朋友的电话。水白感觉自己真是糊涂了。
水白问:“我又有什么东西落下了?”水白那天本来就没带什么,还能什么东西呢?
青青说:“你来了就知道了,你若方便,就到我家来,不方便,我抽空给你送过去。”然后就说了自己的地址,水白一听竟然跟自己住得还很近,也就十分钟的路程吧。
青青又说:“有好一段日子了吧,要不过来坐坐。”
水白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尤其刚才还说到“难道不知道我会等你电话”,水白感觉著自己已经欠了她的了。
挑了个星期六晚上,水白先到花店买了三枝玫瑰。想不出该买什么花,而且对于青青,好像送玫瑰也是最合适的。水白只是本能地这样觉得,然后也就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青青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出来开门。水白一见面就说:“这么早就准备上床啊?”
青青笑笑说:“习惯了洗完澡就上床的,也喜欢晚上只穿睡衣,不喜欢穿白天穿的衣服。”
水白很是腼腆地把手中的三枝玫瑰送到青青目前。青青眼中露出欣喜之色,然后就在水白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水白真是没想到会这样,心跳加速,脸是肯定红得发紫了,整个人感觉刚从高温地带回来。青青倒显得一切如常,领着水白就进卧室。
水白站在卧室门口,竟呆住了。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放在屋子的正中心。没有灯,只有蜡烛,一根根站在床的四围。床罩、被子、枕头都是粉红色,在跳动的烛光下,床本身就是一个年少的姑娘,因为什么独自羞红了脸。
青青拉拉水白的衣袖说:“怎么,不好意思进么?”
水白看看青青,又看看房间,说:“你这张床不用人睡都是好看的。”
青青笑了,说:“真是傻子才会说这样的话。床自然要有人睡才是床,正如女人要有人爱才是女人。”
水白问:“艾子睡了么?”
青青说:“她上寄宿学校的,难得回来。倒也清净。”
水白还想问她的丈夫,又觉得问不出口。
(6)
青青素性拉了水白的手,小心地领着她绕过蜡烛,坐到床上,水白也顺从地坐下。不知道该如何,眼睛也不知该往哪儿放。
青青说:“有你坐我床上,我感觉着我这些蜡烛,还有我这张床都完整了些。”
水白闷著头,大气都不敢出。害怕的不是将会发生的事,而是青青所说的话,还有她言语的温柔。那种温柔是水白从没风闻过的,但又十分能体会这种温柔,而且还是往心里去体会。
水白的手是被青青握著的,也是一样温柔地相握,水白努力着不去体会。可是越不去体会,越是感觉到自己是被一个女人握在了手心。
青青说:“给你看看你的东西吧。”说完一只手揭开被子。水白一看,是自己的一件衬衣压在被子底下,就是那天爬山的时候因为热脱下的,竟然一直都没记起来。
水白不想还好,一想又难免心惊肉跳。这女人竟然把自己的衣服放在被窝里亲近。水白说:“一件破衣服,你怎么没有把它扔了。我自己早都忘了。”
青青说:“衣物跟人亲近多了,也会带着人的习性。相信么?我就从你的衣服里知道了很多关于你的信息。你把这件衣服拿回去,也一定能从中获得我的很多东西。我可是跟它耳鬓厮磨了近一个月啊。”
水白听她这么说,又感觉自己多疑,只是不知这女人有什么样的怪癖。
青青说:“你害羞的时候倒是蛮可爱的,我就喜欢看你害羞的样子。”说完又用嘴唇轻轻去啄水白的脸颊。
水白的身体是僵硬的,可是那被亲吻的脸是幸福地红著的。水白甚至感到了自己心的颤抖,那颤抖首先在十根手指体现出来。青青自然是感觉到了,用自己的手轻轻抚摸水白的手。
两个人坐着半晌没说话。青青看着蜡烛,水白也看着蜡烛。等水白抬头看青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跟青青竟然看着同一根蜡烛。
水白不知道青青在想什么,她的脸是宁静的,应该是很专注地在想一件事情,而且这事情跟水白是肯定没有关系的。但就算没有关系又如何。两个陌生女人坐在一张床上,一个还握住另一个的手,从别人的眼睛看来,应该是很美的,也是温馨的。水白不知道这算不算幸福。
水白也沉入自己心事的时候,青青说话了。青青说:“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是青青第一次叫水白叫得这么亲近。不过水白也没觉得什么,很自然,当然也很舒畅。
青青说:“有两个人,一个自南往北行,另一个自西往东行。两个人在路上相遇了。自南的那个问另一个说:‘你知道往东怎么行么?’自西的就告诉他哪面是东,然后也问自南的:‘你知道往北怎么行么?”自南地也一样告诉了他怎么往北行。然后两个人,一个左转,一个右转,继续前行。”
水白说:“这不就是两只手的交叉和分离么?”然后自己的手从青青的手里脱身出来与青青的手模拟了一下。青青什么也没说,只是笑笑。
(7)
两人后来再说一些话,就一起坐到被子上,面对面。青青还是那么柔柔地,水白感觉著自己已经在一种意念的昏迷之中。
青青说:“水,我化妆给你看吧。”水白说好。青青就起身去拿了化妆盒镜子之类的东西重新面对水白坐下。
水白看着青青的手捏著粉饼在脸上的T字部位轻轻扑著。青青那样轻柔的动作,水白仿佛在那见过,好像是水雾弥漫着一个熟睡的女人,或者风中无奈著等待凋零的花。
青青再用小粉刷在眼睑和眼角抹一层紫色的眼影,水白看着那张脸一下变得诡异起来。
青青说:“从前有一个女子,所爱的人出门远行了,就每天披头散发的很吓人。别的女子都奇怪,说:‘爱人不在,也不要老巫婆似的,还有别的男子看着呢。’女子回答说:‘人在世间,总有三只眼睛看着你,一只是爱人的眼睛,一只是他人的眼睛,一只是自己的眼睛。我现在是用我自己的眼睛看着自己。’”
青青再用眉笔一根一根地画著纤细的眉毛,水白看着她那纤长的手指,还有凝神看着镜子的眼睛,她已经俨然自成一个世界,奇怪的是,水白感觉自己也在她的世界里,小指翘著,心神既在又不在每一根画著的眉毛。
然后是嘴唇,唇线笔画出上下两道弧形。又是刷子,沾著唇红在上下唇细心地摩娑。青青抿一抿嘴说:“水,你知道雨天人的心情会起什么变化么?雨,那是天张开了嘴唇,地上的万物也都张开了嘴唇。你知道人的心情会起什么变化么?”
水白说:“自然是有变化的。如果阳光亲近的是人的肌肤,水则进入了人的身体。”
青青说:“水激起挂念与柔情。”
水白蓦然想到自己的名字里有一个水字,而且青青直呼自己为水。不由觉得怪异,再看看自己身处的房间,更是觉得怪异。
水白说:“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青青说:“难得来一次,再呆会儿吧。”
青青已经把化妆的东西都拿走了,重新在水白的面前坐下。水白看着她,这个女人的脸本来就有点狐媚,化过妆之后,更是妖媚了。可不管怎么妖媚,眼角的鱼尾纹还是遮掩不住的。水白觉得不忍心再看下去,就把眼睛转开了。
青青说:“怎么不看我呢?”她伸手把住水白的脸,水白只好又把眼睛对着她,可是看着她眼里的柔情,水白又不好意思了。
水白说:“我真的该走了。”
青青叹一口气说:“好吧,我送你出去。”
水白很快下了床,一下就冲到了门口。青青说:“你跑什么呢?你的衣服不要了吗?”水白只好等在门口,青青拿了她的衣服,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把水白送到了防盗门外。青青又亲一下水白的嘴唇说:“你要常来看我。”水白说好,然后快步下了楼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发现青青倚在门口还痴痴地看着她。水白头一低,几乎是跑下了楼。
(8)
回到家了,水白的心还慌慌的,说不出为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好像闯到了一个人的梦境里去了一样,既然已经到了人家梦里去了,自然也要做那梦里的事情,可水白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
那被青青放在被窝里厮磨了近一个月的衬衣被水白放在凳子上耷拉着,水白看着它,感觉这件衬衣几乎跟自己无关了。不过她还是忍不住捡起来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只是一股香水味,茉莉香型的,恰巧也是水白喜欢的味道,应该就是青青的体味了。不过这么一种香水味能提供有关青青的什么信息呢,水白想不明白。
水白想干脆把衬衣洗了吧,洗了还是可以穿的。不过她到底没有拿去洗,只是把衬衣用衣架撑了塞进衣柜,然后就几乎把它忘了。
又过了些日子,水白到江边的小岛去办差,小岛上的房子几乎都是石头砌成的,而且有些年月了。岛上的树木也是高大,郁郁葱葱的,树干上爬满青苔。水白在石板铺的路上走着,免不了东张西望,蓦然就看见有一个女子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正梳着长长的褐色的头发。她的头发垂在前面,所以她的整个脸都被遮住了。
水白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感觉那个女人应该是个中年的妇女,穿着黑色的裤子和花色的上衣。她的头发真是长的,几乎垂到地面了。她只是专注地梳着头发,一遍一遍的,水白看着觉得头发已经被她梳得很齐整了,但这个女人好像没有感觉似的,还是那么一遍遍专注地梳着。
到了晚上,水白给青青打了电话,青青一接起电话就说:“我以为你又把我忘了。”她的声音柔软地让水白感觉她整个人都要瘫倒在地上了。水白觉得奇怪,自己还没说话,青青怎么知道是她打的电话呢?
水白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青青说:“我有预感的,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梳着头发,然后梳子就掉到地上了。”
水白哦了一声。水白又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青青说:“说吧,看我能不能解。”
水白说:“你说一个人的头发在整个身体里占什么样的位置?”
青青说:“你来我家吧,我慢慢告诉你。”
水白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不是很喜欢去她的家,就说:“要不周末爬山的时候跟我说吧。”
青青呵呵笑了,说:“不行,这个问题只适合在夜晚回答。”
水白没有话了,那边青青好像感觉到了水白的犹豫,又接着说:“你不想来看看我吗?我几乎每天都等著的。”
水白觉得拒绝这么一个温柔的女子,实在有点不应该,就说:“好吧,我周五晚上去看你吧。”
放下电话,水白躺在床上认真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在冒险似的。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个世界对水白来说总是有很多神奇的地方,而水白是最受不住诱惑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什么也诱惑不了自己,那活着岂不是很无趣,人是被诱惑著长大,诱惑著继续生存下去的。
(9)
近来一段时间,水白发现自己头发掉得特别厉害,冲凉的时候,一小圈一小圈的头发被水冲到白色瓷砖的地板上,能看得很分明。床单和枕头上也分散著一根或者纠结在一起的头发,甚至房间地板上也有。
水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脱发,因为脱发是有家族遗传的,水白的父亲就秃头。水白特意为此事咨询了一个老同事,老同事说:“这是自然地新陈代谢,担心什么,掉了还会长出来的。”水白将信将疑,其实也没很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对人的毛发产生了兴趣。
周五水白直到天黑才到青青的家里,水白觉得拜访一个人,尤其是女人,夜晚比白天好的多,白昼的亮光把一切展现了,让人发慌,但夜光往往把什么遮掩了,但也能把那被隐藏的勾引出来。
出来开门的是艾子,艾子一看是水白,就板起了脸,飞快地朝水白身上吐了一口口水。幸好母亲出来了,青青说:“艾子,你怎么能对姐姐这么没有礼帽?”艾子又朝水白呲呲地做了个鬼脸,然后扭身跑进了屋。
青青很快拉了水白的手,一边掀起自己的睡衣往水白胸前擦,水白被青青在胸前擦著有点难为情,就说:“没事的,小孩子的口水不脏的。”
青青说:“这孩子是被惯坏了,脾气也是古怪,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摸不著头脑。”水白说:“人小时候脾气都怪吧。”
青青看着水白笑,又搂住了水白的腰,青青说:“我看你小时候也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人。”水白被她看着,又这样被她搂着,感觉很是侷促。青青又说:“你来了就好,你是不知道我是怎样等你来的。”
说著就拉着水白的手进了客厅,转了个弯,进了水白上次进过的那间卧室。在卧室门口的时候,水白又吃了一惊。房间里的布置已经完全不同,床没有了,只有一张紫色的大概两米长的沙发,还有靠近窗户放著一张黑色的梳妆台,梳妆台的镜子是椭圆型的,很亮,正对着卧室的门。梳妆台前还有一张皮质的圆座的小凳子,看上去就感觉很柔软。
青青拉了拉水白的手说:“进来啊。”
水白说:“你这房间我都认不出来了。”
青青呵呵笑说:“我喜欢不断地重新布置自己的房间,你会习惯的。”
水白说:“原来那张床呢?”
青青指指沙发。水白认真看了看,才发现沙发其实就是由原来的那张床折叠成的,只是把被褥拿走了而已。
青青拉着水白的手在沙发上坐下,又看着水白微笑。水白更觉得无所适从,不知道是回应她的目光呢,还是把眼睛转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青青说:“你来了,我觉得整个屋子都有生气了。”
水白只是疑惑,跟这个女人其实才不过刚刚认识,为什么她对自己能够这么亲暱呢?
(10)
青青拿了一本黑色的精装的书来,水白发现这书的封皮封底和侧封都没有字。青青把书翻开到一页,摊开了放在膝盖上,水白在书页上发现一根头发,心想可能是青青的头发,刚刚落下去的。
青青问:“水,你在这书里发现什么了?”
水白说:“我没细看上面的文字。”
青青说:“与文字无关的。”
水白说:“那是什么?”
青青用两根手指轻轻捏起了那根头发说:“水,这是你的头发。”
水白有点尴尬地笑笑说:“我还以为是你的头发。”
青青说:“难道你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吗?我的头发怎会是这个样子呢?”
水白认真地看了看青青的头发,乌黑发亮的,水白又用手去摸,发丝比较粗,但还柔软。
青青说:“只有你才有这么纤细的头发,而且是淡褐色的。我看到这头发,就好比看到你了。”
水白有点吃惊,说:“怎么可能呢?一根头发算什么,落掉就没有了,而且不断地有新的长出来。”
青青说:“你若把它看成是你身外的桌子凳子之类的东西,它对你自然没什么。但其实它是比衣服与你更接近的。我在你的衬衣闻到你的气息,但看着这根头发,我就看见你了。”
青青把头发重新放回书页,把书合上,那黑色的封皮在她的手下显得越发诡秘。水白想起在岛上看见的那个梳发的妇女,蓦然想到点什么,就问青青:“你说头发对人究竟有何用呢?”青青说:“毛发使人柔软和隐秘。”
水白想到恐怖片里的女鬼一般都是披散著长长的头发,而且把自己的脸都遮住了。又想到有专门甩头发的舞蹈,又想到古时候的人几乎不剪头发的,只是把头发拧成长辫或者盘在头顶。
青青大概觉察到了水白在发呆,就用胳膊碰碰她说:“想什么呢?”
水白回过神来说:“哦,没想什么。”
青青笑着说:“你肯定在想什么,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
水白被她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我只是觉得头发对人比较奇怪。”
青青说:“那是因为你远离它了,所以你会觉得它奇怪。”
青青这么一说,水白又有点懵了。水白想站起来踱踱步,这样有助思考,但这样莫名其妙地突然站起来,青青肯定会觉得奇怪,所以只好忍着。
这时候艾子跑进房间来,嘴里啃著一片西瓜,另一只手还拿着一片。艾子把一片西瓜递给青青,青青说:“给姐姐吃。”艾子执拗著就要给母亲。青青就接过来,然后要递到水白手里,不想水白还没接过来,艾子一个劈手,就把西瓜打翻在地了。
青青倒没有生气,只是说:“艾子你不能这么调皮。”水白倒是感觉自己对艾子有点生气,但也不好表现出来的。
(11)
晚上水白没有回自己的宿舍,水白心里其实不愿意在青青家里留宿的,青青说:“我这里房间多得是,你若想住这一间,你就住这,不愿意的话还可以到别的房间看看。”水白说:“实在不好意思打搅你,我想我还是回去的好。”青青说:“你这么客气我不喜欢。你住我家,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去爬山。”水白觉得再推辞下去就显得自己不礼貌了,水白说:“那我就睡这沙发床吧。”
临睡的时候,水白去了一趟厕所。客厅很昏暗,水白想起青青说她这里的房间多得是,水白忍不住眼睛在客厅里扫视一圈,感觉也有很多门在黑暗中,只是不知青青在那一道门里边,艾子又在那一道门里边。
水白把房间的门轻轻关好,诺大一个空间里就剩水白一个人了。水白看看沙发床,又看看黑色的梳妆台,感觉自己似乎面临两种诱惑。但水白几乎想也没想,就直接向梳妆台走去。她在软椅上坐下来,就看见了椭圆型的镜子中的自己,不禁有点吃惊。
水白其实每天都会在镜子里面对自己的,但现在面对这扇梳妆镜的水白似乎已不是平常的水白。水白看见镜子中的那个人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又放下了。过一会儿镜子中那个人拿起了梳子开始梳头发,而且把头发都梳到前面来,遮住了半边脸。水白看着梳子在头发上不断地上上下下运动,水白想,头发已经很齐整了,为什么梳子还在不停地梳。
水白猛然醒悟过来,恍然觉得这是不是青青故意安排的,青青就想把自己安置到这样一个房间里。水白环顾四周,心想说不定什么地方有摄像头此时正窥探著自己的一举一动,但除了天花板上花环状的白灯,墙壁上什么也没有。水白又站起来走到门边,门上也没有窥孔。水白很想开了门看看,又觉得不妥,而且心里也有点害怕。
水白又重新坐回梳妆台,这一次她认真地看了梳妆台上摆放的各样化妆用具,大部分自己都是用过的,也有不知道怎么用的。
水白看了看镜中的自己,似乎熟悉了些。然后她开始给自己化妆,从眉毛开始到眼睛到嘴唇,几乎把梳妆台上的所有化妆用具都用了一遍。她站起来远远地看了一下效果,感觉著远看比近看美,可是近看的时候,又发现比远看脸上显得光亮得多。
水白正著身子看,又侧了脸看,她想挑剔一下自己,又似乎没什么可挑剔的。水白想每个人对于自己大概都是如此,无论怎么丑陋的,也能在镜子里发现自己其实也有美丽的时候。
水白在软皮的凳子上安安静静地坐着,就那样看着镜子中的人,像看一道风景一样,所不同的是,水白专注的看与这道风景本身的美丽与否无关。
后来水白觉得疲惫了,就在沙发床上躺下睡着了,房间里的灯应该是一夜开着的。那镜子里的人似乎也还是一夜都在,浓浓的妆,眼睛炯炯地。
(12)
第二天水白起来打开门到了客厅,青青和艾子都起来了,青青正在忙着摆放碗筷,早饭都做好了。青青一看见水白,脸上就起了微笑说:“昨晚睡得好么?”说著又走到水白身边搂着水白的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水白感觉迷迷糊糊地好像还没完全醒过来,又有点觉得不好意思。青青说:“快去洗脸吧,等你吃饭。”水白就转身向洗手间走去,走进了才发现艾子不知什么时候已跑到洗手间门口,岔开双腿和双手把门口挡住。
水白说:“艾子,你要做什么,让我进去洗脸。”
艾子翻着白眼仰著头看着天花板,水白又说:“艾子乖,让姐姐进去。”艾子低头就朝水白呸了一声,水白以为她又要吐口水了,闪了一下身,艾子却没有吐出口水来。
青青听见声音过来了,拉了艾子的胳膊说:“又捣鼓姐姐了,乖,坐饭桌边去,一会儿吃饭了。”艾子一甩母亲的手很快跑开了。青青又搂搂水白的肩说:“快去,等你出来。”水白诺诺地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觉得很不习惯青青这样的柔情蜜意。
把洗手间的门关了,水白才猛然想起自己昨晚化的妆还没卸掉,她一下扑到洗手池边,镜子里的水白一点化过妆的痕迹都没有,全然就是平常的素面朝天的水白。水白努力地回想昨晚睡前的那一断时间,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卸妆就困得躺下的。水白想了好一会儿,觉得越想越复杂,怀疑自己是做梦了。
洗簌完出了洗手间,青青拍拍自己身边的凳子说:“快过来吃饭。”青青看起来心情很好,水白感觉她看到自己眼睛就发亮,整个人也随之精神洋溢。水白不由得感到隐隐的惭愧,因为她明白自己对青青不可能有这样的深情。
稀饭也都已经盛好了,青青用干净的筷子给水白夹了干鱼片,不过很快艾子的筷子就伸过来把水白碗里的鱼片夹走了。青青柔声看着艾子说:“艾子不许这样对姐姐。”其实青青已经给艾子的碗里夹了各样菜了。
水白倒觉得过意不去,说:“我自己来吧。”
青青说:“这鱼片国内买不到的,听说滋阴补阳,你多吃点。”说著又重新夹了几片到水白的碗里。水白说:“够了,我自己来,你也吃。”
水白扒拉了几口,不经意抬头,发现青青正看着自己微笑。青青说:“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饭了,看着你吃就觉得很满足。”水白怀疑青青的丈夫大概不常回家,难得有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所以现在看着一个陌生人吃饭都觉得满足。
水白自己感觉脸红了一阵又一阵,又想到这样红著被青青看了去,更是觉得羞愧难当。青青似乎倒不觉得异样,除了给艾子夹菜,就是微笑着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水白吃。水白想起自己的初恋的时候,跟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一起出去吃饭,脸似乎也是这样一阵红一阵的。但那时脸红是因为自己喜欢那个男孩子,害怕自己出丑,在青青面前脸红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13)
下午爬山,艾子在前面,青青拉着水白的手缓缓跟在后面。两个人闲闲地说一些话,但即使两个人都不说话的时候,青青也不时转头看水白,眼睛盈盈的,旁若无物。水白还是觉得自己不能习惯青青这样的亲暱,尽力不去接青青的目光。有时候青青走累了,会停下脚步,水白也停下脚步,青青揽著水白的肩,用手去拂水白垂在眼前的头发,水白低着眉眼,不敢看她。
青青说:“怎么不看我呢?”脸上浅笑着。
水白脸红红地转过头去。
青青说:“你真是很害羞的孩子呢。”
水白说:“我不是孩子。”
青青说:“在我心里就是孩子了。”
爬了一些时候,青青说累了,就在路边的亭子坐下来。亭子中间有一根碗大的木头柱子,艾子一只手拉在柱子上,绕着柱子不停地转,转了十几圈了,也不停下来,看得水白都晕了。水白说:“艾子,你不晕么,快停下歇歇。”艾子还是那样转着,似乎也没听见水白的叫声。
青青说:“山上的空气就是好。”
水白附和道:“是不错。”
水白蓦然想起一个问题来,跟青青说:“前几天有个男同学跟我说,她女朋友性冷淡,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青青哦一声说:“有这么回事?”水白说:“是。”
青青说:“水,你相信有真正性冷淡的女人么?”
水白说:“大概有吧,因为身体或心理的障碍。”
青青说:“水,没有真正性冷淡的女人,只有深藏的未被挑逗的激情。”
水白想了一会儿说:“怎么解释?”
青青说:“好比地底的水,有些从石缝里流出,有些并没有流出来,人们就说可能是因为碰到了阻碍或者那个地方没有水。其实水无处不在,只是还没有让我们看见。”
青青又说:“就拿我来说,只要你看着我,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倘若我现在还没有做什么,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着我。”
水白说:“怎么会呢?”
水白说怎么会的时候,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话有点含糊,究竟是指青青怎么会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呢,还是说自己怎么会没有看着青青,水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指的是那层意思。
水白问青青:“你为什么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呢?”
青青看着水白说:“因为你看着我呀,对于我来说,你看着我就足够了,但有些人,她们可能觉得光看着她们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别的事情。”
水白还是有点疑惑,但似乎也明白了些。水白倒是觉得,其实自己也不用怎么看着青青,青青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水白想起小孩子,可以不管大人是不是在留心他,也可以玩得很开心,但青青自然跟小孩子不同。
(14)
临别的时候,青青拉着水白的手问:“什么时候来看我?”水白支吾著不知怎么回答,青青又说:“要给我打电话。”水白说:“会的。”水白转身要走,青青又拉住她说:“等等。”水白站在原地,青青说:“你衣服上有根头发,好了,走吧。”水白忍不住说:“谢谢。”青青拍拍水白的脸颊说:“不许说这样的话。”水白脸又红了。
回到家,水白第一个冲到洗澡间,洗了澡,换了衣服,她感觉自己从很远的地方归来,风尘仆仆。直到把换下的衣服都洗了,水白才放心地在凳子上坐下来。水白随手拿了一本杂志翻开,一眼就看见一张大大的摄影作品,照片是在街头拍的,是一个低头理著自己货物在路边摆摊的人。照片看起来很宁静,或者说大街的喧闹跟这个低头的做小买卖的商人没有关系,没有眼光注意到商人此时的动作。
水白拨了青青的电话。青青接起电话说:“我刚才正想着什么时候我才能不被你看见。”水白不由愣了一下,水白说:“我现在不就看不见你么?”青青说:“你以为你看不见,其实你的眼睛已经在我心里了。”
水白看着手里的那幅摄影作品说:“我也正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一个人有眼睛看着跟没有眼睛看着有什么区别呢?”青青说:“人只有两种状态,要不暂时忘却那看着自己的眼睛,要不迎接着那看着自己的眼睛。”水白说:“那有什么区别呢?”青青说:“可以说没有区别,只是对那看的眼睛有无自觉意识罢了,但人是要被看着的。”
水白心里想说:“我倒不觉得自己有被谁看着。”不过她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自己看着镜子中的那个人,水白就没说了。
水白对青青说:“我对你了解不多,你对我也了解不多,我们其实彼此都还很陌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可以对我这么亲暱。”
青青低低地笑了一声说:“你觉得爱一个人非得要彼此了解很深很透彻吗?”
水白说:“按理说了解一个人越多,爱得也越深。”
青青说:“爱首先是感觉,其次才是关系。但在你心里,爱首先是关系,其次才是自己的感觉。”
水白一时想不起该说什么,青青又说:“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呢?”
水白说:“大概要过一些时候,这几个星期都没有空。”
青青说:“我会想你的,你也要想我。”
水白说:“应该会吧。”
这时电话里有砰的一声,好像是青青旁边的凳子倒地上了。只听青青远离了话筒说:“艾子,你又调皮了。”不过很快青青又对准了话筒对水白说:“我希望你早点来。”水白说:“尽量吧。”青青又说:“我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枕头,感觉是抱着你,反正你离我不远。”
水白支支吾吾地又不知道说什么,转念一想,也许青青也并不需要自己说什么,她说了,而水白也听见了,这就足够了。快放下电话的时候,青青说:“水,你告诉我一个你从没告诉过别人的秘密吧。”水白想了想说:“我在7岁的时候把死去的家狗埋梨树下了,家里人只知道狗死了,却一直找不到尸体。”
(15)
几个星期之后,水白又到江边的那个小岛办差,她又走了上次看见梳发女子的那条路,但这一次在那石阶上一个人也没有。水白在岛上唯一的一所小学门口经过,学校门前的石板空地上,有小学生在踢足球,水白经过的时候光看着那个被踢来踢去的足球,感觉它随时可能击中自己。
办完公事,水白决定不走原路回去,而是走了另外一条比较僻静的路,因为岛很小,水白不担心会迷路,反正总是能找到桥回陆地的。水白一路只仰脸看着路两边高大的树木,一不留神,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岛上唯一的一所小学校门口。校门前的石板地上竟然一个人没有,刚才那些热闹地踢著足球的小学生已经无影无踪。水白猜想大概上课了吧。
水白在校门口石板空地上的一个石墩上坐了一会儿,也没见到一个人经过。她看看四周,发现自己四围有通向四面的路,水白想是否岛上的每一条小巷最终都通向这所小学校。
晚上临睡前,水白给青青打了个电话。水白听见那边电话接起来了,却许久没有声音。水白又喂了一声,话筒里又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水白听见青青的声音:“你不说话我也知道是你,而我不出声,你却不知道是我。”水白含糊地说:“我没有你那样的直觉。”青青说:“与直觉无关,不过是盼望的心的敏感而已。”水白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周末我去看你。”青青说:“好,你来。”
距离周末还有几天,水白先去修理头发。水白的头发已经及肩了,水白对理发师说:“不要剪断,末端修整一下就可以了。”理发师说:“小姐的头发不错,好好护理可以很漂亮的。”水白闭着眼睛没看镜子中的自己,也没回答理发师。对水白来说,只要保持头发干净和柔顺,出门就没问题。
修了头发,水白又去百货女衣层转了一圈,买了一件针织上衣和一条杏色的纱裙。水白想这样应该足够了。
一切准备好了,水白出了门,在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水白突然想起自己还穿着休闲时穿的平底鞋。水白立即掉头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换了一双尖底的高跟鞋,鞋跟很细,水白在鞋跟加了软垫,这样走在水泥地上,就不会有清脆的踢嗒声了。
在公交车上坐着的时候,水白想自己是否太把这样的一次见面当回事了,仿佛是一次郑重的与男友的约会。但激动的心情是没有,水白看着公交车上上下下的男女,看男的时候,水白光看他们穿着的上衣衣领,看女的时候,水白注意着她们的手腕有否带好看的手链。
快下车的时候,公交车上来一个穿黄色体恤的男人,水白发现这个男人一看见她,就一直盯着她,并朝她走过来。水白也看着他,感觉似乎面善,水白努力回想是否跟这个男人认识,不过脑子里一点印象没有,她还是看着他,等他过来与自己相认。黄色体恤的男人看着她走到她面前,然后从她身边过去。
水白没有掉头再看她,并且相信这个黄色体恤的男人也不会再转头看她。水白把眼睛转向窗外,看见一个站在马路边搔首弄姿的女子,黄色的鲜亮的头发,卷曲的,披散在两肩。水白看见这个女子旁边还有一个小男孩在玩手中的玩具车,似乎是这女子的孩子,似乎又不是。
(16)
下了公共汽车,水白几乎没怎么留心自己的脚步,就到了青青的家。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水白就看见了青青家的防盗门开着,里面的一道木门则虚掩著。水白觉得有点奇怪,心想是不是青青已经等著自己来了。
水白摁了一下门铃,等了好些时候,也没人出来,水白又用手指敲敲木门,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人出来开门。水白想青青和艾子是否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听不见门铃和敲门声。水白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客厅的灯亮着,没有人。水白叫了一声:“青青。”没有人应,水白又叫了一声:“艾子。”还是没人应。客厅甚至还有点回音。水白发现,客厅通向其他四个房间的门只有一道是开着的,就在自己左边,也就是水白住过的那个房间,其他三道门都紧紧关闭。
水白一转弯,就进了灯火通明的自己住过的那个房间。一进门,水白就在与自己面对的墙上看见了自己,不由得停下脚步。房间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三面墙上都安装了高高的镜子,水白往左边看,看见了孤立地站着的自己,往右边看,也是有着迷茫的神色的自己,往前看,还是自己。
水白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想赶快退出这个房间,感觉双脚铅块似的沉重。就在这时,门口有响声,是青青和艾子回来了。水白一个踉跄出了房间,与进来的艾子撞个正著。水白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艾子一个甩手,就把手里正吃着的冰激凌扔到水白的脸上。
只听青青说:“艾子,怎么又欺负姐姐。”水白一边用手擦脸上的奶油,一边看着青青尴尬地笑着说:“我以为你们在家,所以就进来了。”青青说:“我和艾子出去买点东西,门是特意为你开的。”
不过一会儿,青青已经拿了毛巾出来,给水白擦脸上和胸前的冰激凌,艾子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看。
青青说:“每次你来,艾子都捣蛋,我道歉。”说著在水白脸颊上亲了一下。水白连忙说:“没什么,小孩子爱玩而已。”青青说:“水今天看起来很漂亮呢。”水白不好意思地低头,青青又用手托起她的下颌来看,水白更难为情了,青青说:“你这害羞的,好像从来不敢看自己。”
青青拉了水白的手把她引到电视机前的沙发坐下,青青对艾子说:“陪姐姐看会儿电视。”说完她进厨房去了。艾子原本一直没看水白一眼的,青青转身走后,艾子转脸狠狠白了一眼水白,水白没有理会她的白眼,温和地说:“艾子喜欢看什么节目呢?”
艾子眼睛盯着电视没有说话,一只手拿着电视遥控器,看一会儿举著遥控器对准电视机换一个频道,同时微微侧脸白一眼水白,就这样看着换了好几个频道,水白被她白眼看得渐渐地觉得心里很窝火,想站起来找青青去,青青已经端著两盘水果从厨房出来了,水白只好又重新在沙发坐下。
(17)
水白问青青:“你那房间怎么又改样了呢?”青青把一片西瓜片送进嘴里,咀嚼著微笑说:“喜欢吗?我现在把它作健身房了。”青青把手中的牙签放下,拉住水白的手说:“来,我带你去看看。”
水白坐着没动,水白推辞道:“我看过了。”青青眼睛看进水白的眼睛里去说:“怎么,你害怕了?”水白赶忙分辩说:“没,怎么会害怕呢。”青青笑着说:“那就是了,来,随我来。”水白只好起身跟在青青身后进了那间屋子。
青青说:“你看,只要我们不掉头退出这个房间,我们无论走向哪里,其实都在走向我们自己。”水白极力低头不看镜子。青青也察觉了,青青伸一根手指把水白的头提起来说:“看啊,你害怕你自己么?”
水白强撑著抬起眼睛,但她也只看着镜子中的青青,而不是自己。青青看着镜子中的水白说:“别看我,看你自己。”这一说又把水白的头说低下去了。
青青说:“我带你跳舞吧。”青青一手揽了水白的腰,水白迟疑着把左手攀在青青的肩上。没有音乐,但两人配合的很是默契,让水白都觉得奇怪。水白的头贴著青青的肩,眼睛看着镜子中青青的背影,但慢慢的,她也看见了自己。
舞步不知什么时候有慢四转成了中三,水白只看见自己在不停地旋转,她已经很清晰地看着镜子中的那个人了,头微微地后仰,一只手在青青的手里,一只手柔软地搭在青青的肩上。迷糊中,水白感觉那个人似乎已经飘起来了,像不着地的落叶一样。
水白听见青青说:“你以为你看见的不是你自己么,她就是你,或者你的影子。”水白说:“我不觉得她就是我。”青青说:“水,你为什么不愿意她是你呢?”水白僵住了,不知怎么回答。
青青要送水白下楼,水白坚持不让她送,水白说:“我自己回去就是了,免得一会儿你还要爬楼梯。”青青说:“我乐意送你,你最好不要拒绝。”水白就不再说什么了。
水白双手提着裙子,怕自己脚踩了裙角摔倒,青青则一手搂着水白的腰。青青说:“水,这以后的日子恐怕会更想念你。”水白说:“为什么?”青青说:“因为你离我更近了。”水白不是很明白,但又觉得再问也没有意思,就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已经走下了楼梯,水白心里起了疑问,对青青说:“你说镜子是什么呢?”青青伸手把水白的头发拨拉一下说:“没有什么,我们需要的一种意境而已。”水白看着远处的花丛里有一只猫一闪身就不见了,心想这大晚上的,应该是只野猫吧。
青青把水白一直送到马路边,看着水白上了的士车,水白头从车窗探出来说:“青青,你回去吧。”青青站在原地看着水白微笑。的士车已经开动了,水白突然又想起什么,提高声音问青青:“青青你说房间是什么?”青青还是那样矗立著,白色的连衣裙被风吹乱了。青青沉稳的声音说:“各自睡榻或者坟墓吧。”
(18)
周末在街上逛著的时候,水白突然想给青青打个电话。水白拐进一条车辆和行人稀少的街道,手机拨了青青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声音很粗,水白有点发愣,压根没想到会是个男的。
水白说:“请问青青在吗?”那边那个说:“青青,没有这个人。”说完电话很响的挂断了。水白有点迷糊,再仔细看看电话本里记着的青青的电话,没有拨错号码,水白又拨了一次。这一次是一个女的,她说:“青青,我们家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水白慌慌地把电话挂了。她想起青青是有手机的,于是找到她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很快水白听到有机械的女声说:“此电话号码已暂停使用。”
水白还是觉得不甘心,心想一个人怎么可能消失得这么快呢。她拦了一辆的士前往青青的家。下了车,水白觉得即使自己闭着眼睛,也还能找到青青的家,她一路半跑着上了楼,在青青家门口的时候,水白稍微站着缓了缓气,然后摁了门铃。
几分钟后,有人来开门,是个年轻的女子,棕色的卷发,很长,垂在两肩和胸前。她很有礼貌地问:“请问你找谁?”水白心突突地跳着,自己也不明白紧张什么。水白说:“上个星期这房子住的是名叫青青的女人,请问你认识她吗?”年轻的女子愣了一下,然后回过神来似的说:“哦,你可能找房子以前的主人,抱歉,我昨天才搬来住。”水白还想再问,但看女子迷茫的样子,水白只好说:“对不起,打搅你了。”
水白也没有兴致再逛街了,直接坐公交车回了家。一到家,水白先站在镜子前面,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神色,脸有点红润,眼睛也还是有神的,但水白还是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在房间里走了几圈,水白猛然想起衣柜里自己那件被青青搂抱了一个月的衬衣,她打开衣柜把衬衣从衣架上取下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茉莉的香味还隐隐约约地在,但闻久了,水白又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她抱着衬衣在沙发坐下,想不出个头绪来,觉得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不知该如何想起。水白脑海里飘过蜡烛围着的粉红的床,黑色的梳妆台和三面镜子的空荡荡的屋子,除了这些似乎就什么也没有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那件衬衣被水白放在自己睡的被窝里,因为冬天已经来临,水白也懒得把它取出来重新放进衣柜。茉莉香味应该是没有了,但水白还是恍惚闻着了那衣服里不属于自己的气息。
大概一个月之后,水白接到一个电话,一听见声音水白的心就狂跳起来,是青青。还是那么柔和的声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青青说:“水,想我了吗?”水白说:“你现在在哪里?”青青说:“我在国外,大概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