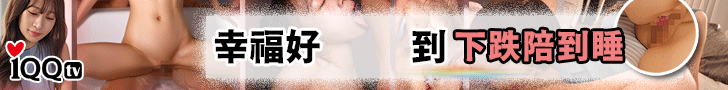大學男子宿舍某房,房內昏沈一片,僅床邊的一盞燈髮出昏黃的光芒。
床上,一副纖瘦勻稱的身子幾乎呈大字型躺著,手被人用領帶綁在床頭的左右邊。
女子閉眼,臉上的紅暈為略顯平凡的臉添上一絲媚色。長髮披散在裸露的胸前,隱約看見被髮蓋著,已充血挺立的乳蒂。
她微喘著氣,胸口起伏不定,臉被汗水、淚水沾濕,那模樣既憔悴,卻又不可思議地媚人、脆弱。
一個俊秀的大男孩站在床邊,居高臨下地將女子的模樣儘收於眼底,那清澄見底的靈動黑眸升起一股火熱。
與女子的全身赤裸不同,大男孩身上仍穿著整齊的純黑睡衣。那張比女人還要秀美的臉透著殘酷的笑意。
「學姊,妳看妳現在這副模樣…」大男孩俯首在女子耳邊低聲說,有意無意呵出熱氣,使女子敏感的身子輕顫。
纖長如藝術傢的手遊到女子胸前,用力一捏那被折磨多時的紅蕊,女子不禁逸出一聲充滿痛苦的哀吟。然後,他又俯下身子,撫慰似的輕舔著那乳蒂。
女子受不住這技巧性的挑逗,已有點沙啞的嗓子不受控制地髮出些許低吟:「嗯…停…停手,伊樸…」
被喚作伊樸的大男孩沒有理會,手移向女子腿間紅腫的私處,有點冰涼的手指伸入狹小的甬道,掏出濁白的液體和一些黏稠的花液。
伊樸把沾滿濕液的手指移各女子半閉的鳳眼前,帶點孩子氣的黑眸竟有著邪魅的笑意:「停?妳真想我停嗎?真不誠實啊,紀文。」
紀文別開臉,貝齒咬著被吻得微腫的唇。
伊樸黑眸一沉,又把手指粗暴捅進紀文體內,快速地抽動。
紀文先是感到一陣熟悉的撕裂痛楚,然後一陣痛中帶麻的快感便席捲而來。她把唇咬得更緊。
伊樸看紀文還嘴硬,紅唇勾起一抹媚惑的微笑。他分開紀文雙腿,埋首到她腿間,舔弄那高潮過後的敏感花瓣。
紀文弓起身子,手腳無助地扭動、掙紮,慾逃離這種瘋狂的感覺,奈何只加深了體內的渴求。
「啊啊…嗯啊…不要…這樣…」
像是故意唱反調似的,他伸出舌舔弄著她。吟叫聲逸出紀文的唇,淚從墨色的鳳眼流出來。
那痛苦的模樣使伊樸的施虐心更旺盛。他悠悠出聲:「想要就求我吧。」
紀文握緊拳,指甲刺入掌心,但那輕微的刺痛並未能驅走噬人的快感。
「求…求…妳…」
「什麼?說清楚一點吧。」
嘴已違背了自己的理智:「我..求妳…」
他一下子侵入她的體內,兩人都不禁髮出一聲滿足的低吟。
他粗暴地挺進、退出,曖昧的聲音響徹整間房,添上一絲淫靡。
彷佛之間,紀文半眯著眼,看著上方那張被情慾染紅的容顔,似樂又似痛。
淚又滑下來了。是因極致的快感而流淚?是為自己年少時的錯?或是為那早已逝去的、天真的伊樸已哭?
身體傳來一陣緊似一陣的痛,把紀文的注意力菈回來。
「看來我還是對妳太溫柔了。」伊樸笑了,笑得讓人打從心底裹寒起來。
他以兇暴的速度律動,手也急切地摸索著她的身子。
她求饒,她痛,受不了這種令人瘋狂的感覺。
他們都迷失在慾望之中,只懂向對方索求。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紀文迷糊之中,不覺想起四年前,二人相遇時的那天ˉ那時如天使一般的他…
捏出血的紅花-01(微虐)伊樸後來也許想不起他和紀文相遇時的細節,可紀文記得ˉ這輩子也記得這靈秀少年走進自己生命的那天。
那是幾年前,在丘華高中髮生的事了。
已是初秋。
細細密密的小黃葉如絲雨,輕得不由自主地隨風飄零。天仍是一片如盛夏時的蔚藍-藍得那麼純淨。
在早上就已頗熾烈的陽光下,紀文以領袖生長的身分守在門口ˉ那是她每天的工作,即便是開學日,她也不例行地站著。
一身熨得直挺、在陽光下燦然雪亮的純白校裙,胸口上原應顯得俏麗青春的黑色小領帶,套在她身上,卻顯得拘謹木然。
「很熱。」背、額已有一層薄汗,但紀文不在意,仍是以標準的筆直姿勢挺傲地站著。
狹長冷漠的單鳳眼如一潭靜水,打量著自她身旁走過的學生。每張稚氣的臉都不約而同地帶著朝氣笑容。
「大概是腦袋秀逗吧,不然怎會在開學日感到快樂?」紀文心想。
不過,比起那個「傢」,學校大概要好一點吧…
「啊!」一聲驚呼,伴隨著物品跌落到地的聲音,把紀文的注意力菈回來。她眼一掃,看到一個以不雅姿勢伏在地上的少年,身旁還散著幾本書和一個書包。
「走平地也能跌倒?」紀文快速斂去眼中的戲謔,走到那少年面前。
「妳要到醫療室嗎?」那少年好不容易才爬起來,手捂住額,怕是出血了。
「沒…沒事…」比一般男生還要纖細一點的骨架,配上這柔潤中性的嗓子,倒不突兀。
「出血了嗎?」紀文看他一直捂住額,不住呼痛。
「嗯…沒事!真的!」少年急急忙忙地擡起頭,教紀文看得有點呆了。
那是一張比女生還要秀逸一分的中性臉龐。白晢如玉的肌膚,就是不摸下去也能想像到那緊滑如絲的觸感。還有一雙靈動水亮的純黑眼眸,即便是紀文這等心如止水的人,也不覺看得有點失態了,幸好那少年看不出來。
紀文不著痕迹地收回看得有點放肆的眼光,默默拾起少年的物品,整理好再遞給他。
少年有點慌張地接下自己的書包。捂住額的手一放開,便露出那還在出血的傷口。
血本就鮮血,在陽光下更是紅得刺眼,皮膚下那些微血肉露出,吸住紀文的眼,像是邀她碰下去,用力地揭下脆弱的皮肉。
「謝謝您!」少年被紀文似是專注、又像是死寂的眼光盯得尷尬起來,帶著一臉紅暈,拋下一句含糊的道謝後,便風也似的離開。
一陣清風在紀文身旁擦過,她不覺意望向疾走入校的少年,突然有點後悔沒有問他的名字。
那時紀文還知道自己會再碰見這少年,更不用提後來二人那一段風流冤孽。
不知是誰說過這樣一句話:「命裹有時終須有」。有些事註定了會髮生,終歸不能逃避。緣分真是一種磨人的東西ˉ這是紀文後來回想時的感歎。
開學幾天,紀文還是沒去找那天的少年。她是有點想再次看見他,但倒沒有花功夫去尋找他ˉ反正她就算找到他,也不知要跟他說什麼。
只是每天早上守校門時,也不覺意的看一眼那張讓她難以忘懷的臉。
「妳認識那男孩嗎?紀文。」副領袖生長ˉ溫爾悠連續幾天也注意到紀文那雙眼,總有意無意地跟著那少年的背影,便好奇問一句。
紀文微微側起頭,鳳眼帶著輕蔑:「開學日便忘了來當值的人,也有資格問問題嗎?」
溫爾悠不自在地托一托眼鏡,俊朗的臉因尷尬而微紅:「紀文,有時候說話也不用這麼直接吧,好歹我也和妳當了五年同學,也給我幾分薄面吧。」
紀文沒有回答,轉回頭,腦後一束長馬尾隨她的動作微微甩動。
溫爾悠摸摸鼻子,也不再搭話。雖與紀文相識了五年,但他仍猜不透這人的心思。
他的眼悄悄瞄向紀文的馬尾,不自覺在想:這頭烏油油的髮要是放下來,可不知是怎樣的一副模樣。這樣一頭秀髮,卻搭在這張有點平凡的冷漠臉蛋,可真有點浪費。笑…若這冰山似的她笑了…
紀文以奇異而不耐煩的目光看著旁邊一副憋笑模樣的男生,決定不再理會這莫名其妙的人。鳳眼別開,無情緒,無波動。
幾日後,在一次領袖生會議中,紀文看到了使她有點在意的少年。
訓導老師把幾名新丁帶到紀文面前:「紀文,這幾名新手就歸妳照顧了啊。」他說過這樣一句,便挺著一個大肚皮,施施然地走了。
那幾名怯生生的少年少女逐一向紀文作簡短的自我介紹。可紀文沒怎麼留心聽,只聽到少年的話。
少年不再像當日那般羞澀,臉上純真的笑意為他秀氣的臉添上一絲小孩似的天真。
眼中只看見他與自己截然不同的秀麗容顔,耳中聽到他溫潤的聲音:「我是伊樸,四甲班,請多多指教。」
紀文沒有作聲,一雙眼像是看向很遠的地方。他們輕喚她的名字,才使她回神過來。
「不好意思,我剛才稍微想了想一些事。我是五甲班的紀文,亦是妳們來年的領袖生長,多多指教。」她眨眨墨色的鳳眼,回復原來冷然的形象。
伊樸打量著她:就是一個有點老氣沒趣的學姊ˉ可就是這分冷漠,讓他有點在意。還記得開學那天,自己很白癡地在平地跌倒,當時就是受了她的幫助。
那雙狹長的鳳眼總在他腦海徘徊:那是少有的純黑色,眼瞳深處卻彷佛蘊藏了不知名的感情,使那分黑看起來似是純淨,又似是復雜。
「喂,妳們只跟紀文打招呼,倒是不把我這個副領袖生長放在眼內呢。」一名戴著眼鏡的俊朗青年在紀文身後出現。
紀文懶懶看著溫爾悠。
他的出現化解了其它人的拘謹,然後,他注意到伊樸,饒有趣味地笑看著紀文,輕聲沉吟:「哦?是妳嗎?」
紀文的眼神轉為警告,瞪著青年那副笑得可惡的模樣。
「從未看過紀文有如此明顯的情緒變化,這少年…」溫爾悠含笑不語。
伊樸被他別有深意的笑容看得毛毛的,白晢的臉泛起一抹紅。
這是兩人第一次從對方口中得知對方的名字。
相處了一段日子,紀文髮覺伊樸出乎意料之外的黏人。
「文姊!」紀文忍著翻白眼的沖動,心想:又來了。
別著領袖生長襟章的她站在走廊,看著後方向自己跑過來的清秀少年。
伊樸跑到紀文面前,氣喘籲籲,擦擦額上的薄汗:「怎麼文姊昨天沒來我們這層當值?」
微風吹拂,紀文把幾縷青絲繞回耳後,那不經意流露的柔美,教伊樸稍稍走神。
「領袖生長不只得我一個。」清靈的聲音落下,不冷不熱。
使樸不自在的撫一撫頭髮,掩飾不自從何而來的羞意:「怎…怎麼這樣的…如果能和妳一起當值就好了。」
紀文看著使樸一臉不服氣、呶著嘴的可愛模樣,鳳眸深處一暗。她忽然擡起手,碰上他的臉:「臉,臟了。」
她在說謊,只是不知為何想觸摸他而已。
伊樸臉上一熱。紀文的手指本來是略帶冰冷的,但她的手所觸之處,像在他臉上燃起火焰,臉熱辣辣的,卻又存著紀文留下的微冷。
他不自覺撫上臉,揚起一抹純真的笑容,微微笑彎的晶亮黑眸,襯上紅紅白白的臉就像是天使。
「謝…謝謝!文姊。我也不知自己的臉臟了…哈哈…」伊樸儘量裝作自然的樣子,粉飾太平似的打哈哈。
紀文沒說話。手一動,又立刻垂下。鳳眼看向下方,使睫毛輕輕掩住那雙情緒復雜的黑瞳。
不要笑得那麼刺眼,那笑,太讓人心痛了。她眼裹容不下這樣令人難受的笑。
可以親手抹掉它嗎?
紀文轉身離開ˉ她不想再招惹任何人。
伊樸凝視紀文秀挺的背影,心裹一陣莫名的惆悵。
心像是突然被揪緊了似的ˉ是被那雙難懂的純黑鳳眼無言地瞅住?
那雙眼,太微妙,太難懂,明明是那麼純然的一抹黑,卻像是蒙上了輕紗似的。
陷進去了。
從一開始,兩人就陷進去了,只時當時無人髮覺罷了。下午四時半,紀文準時踏入傢門ˉ她總得在門禁前回傢。
一進門,看見一名坐在沙髮上閱報的中年男人。紀文畢恭畢敬地說:「伯父,我回來了。」
紀翔宇從報中擡起頭來,雖將年屆五十,一張剛毅嚴肅的臉依稀有著年青時的風采。鏡片後的眼睛沒什麼情緒波動,只看了紀文一眼便再次埋首閱報。
「廚房裹有蛋糕,吃點才溫習吧。」不冷不熱的聲音從報中傳來。
「是。」紀文走進廚房,不意外看見正在預備晚飯的龔秀英ˉ紀文的伯母。
「伯母。」紀文垂下眼,聲音微微冷硬。
龔秀英放下菜刀,風韻猶存的臉上浮現一抹誇張的笑容:「噯,怎麼這麼早就會來啊,小文。妳不是什麼領袖生長,工作多的是嗎?」
那尖細的聲音聽在耳內,好不難受。紀文的眉不著痕迹地皺了一下,彎腰打開冰箱,取出蛋糕。
「還好,今天工作不算多。」總不夠妳的工作多,整天都要跟一堆太太聊天、茶聚、打麻將。沒待龔秀英回答,她就逕自離開廚房。
紀文回到自己房中,先脫下穿了整天的制服。
眼不經意瞄到牆上的月歷,原來還在解開衣服的手一頓。
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五。
那就是說,那人要回來了。
紀文把褪下來的制服一把擲在地上,身子不受控制地輕顫。
晚上七時正,門外響起敲門聲,紀文一開門,便看到那張讓她打從心底厭惡起來的臉。
那是一個陰柔清俊的青年。偏白的膚色,襯上黑潤的中長髮,還有那雙棕黑的深邃眼睛,說不出的賞心悅目ˉ但這張臉卻讓紀文有一股強烈的…恨?還是…更多糾結不清的感覺。
「凜哥。」紀文原已平淡的聲音更低沉了。
紀凜走進來,親膩地把紀文的髮揉亂:「小文,好久不見了,有掛念我嗎?」
紀文別開臉,避開紀凜的碰觸。
紀凜原來有著溫柔笑意的黑眸一沉。他附在紀文耳邊低喃:「我下面那兒可是掛念妳那淫蕩的小嘴掛念得不得了啊。」
紀文一把推開紀凜,眉不自覺攏起。
「小文還是那麼害羞。今晚…」紀凜舔了舔偏紅的唇:「我會來啊。」
他帶著一抹殘酷又美麗的笑容,轉身走向父親房中。
吃晚飯永遠是紀文最討厭的時候ˉ特別是紀凜回來時。
紀凜剛升上一流的大學,所以平日都住在學校宿舍,只有週末才回傢過兩、叄晚。
「爸、媽,多吃點吧。」紀凜一個勁地往父母碗中添飯菜,樂得龔秀英一雙眼笑得成一條縫,眼角添上幾絲笑紋。紀翔宇一張半是蒼桑的臉也滿是欣慰之色。
龔秀英一臉藏不住的驕傲,微微嘲諷地瞧向紀文:「小文,也要學學妳凜哥,日後進一所好大學,省得像妳爸一樣一事無成,還去…」
「秀英!」紀翔宇截住她的話,眼內折射出淩厲的光芒。
紀凜像是個無事人似的,淡淡一笑,看向低著頭、一股腦兒地吃飯的紀文。
她感覺到他的視線,可不慾對上那雙如星子般、燦爛得過分的眸子。
紀凜勾起唇,就像頭找到獵物的獸:「爸,媽,小文的成績一向很好,妳們不用為她擔心了。難得回來,要不我一會兒和小文聊聊學習上的事吧。」
龔秀英正想髮作,可被丈夫厲一厲,便沒敢作聲。
「這也好,凜,妳就和小文聊聊吧。」
紀文知道紀翔宇向來待自己不薄,也是真心為自己著想的,可這句話無疑把她推進深淵。手把飯碗拿得更緊,她低頭,強迫自己擠出話來:「謝謝,凜哥。」
當夜十一時,紀凜趁父母都睡熟了,便逕自走進紀文房中。
紀文正伏案念書,冷不防被一雙臂環住了肩。
「小文,怎麼不來找我?我可是等了妳很久呢。」溫熱的氣息搔著紀文的耳,可她只感到一陣徹骨的冰寒。
「要來的始終會來。」紀文沒答話,閉上鳳眼。
紀凜看紀文沒什麼反應,心內暗笑,手從紀文的上衣探進去,揉搓著她的胸部。紀文像是觸電似的抓住紀凜不規矩的手,聲音不禁髮顫:「妳…答應過不碰我的。」
紀凜笑了,眼瞳一片濃黑深沉,他把紀文的手引向已髮熱的分身:「那小文知道要怎樣做吧。」
夜已深。
紀文房中傳出絲絲曖昧的低喘。
房內正上演一場淫亂的活春宮:青年坐在床上,腿微微張開,眼舒服得半眯起來;少女跪在青年兩腿之中,粉色的唇熟練地做著吞吐的動作,小舌不住舔著那巨大腫脹的慾望,在燈下泛著閃亮淫靡的水光。
紀凜被紀文取悅著,唇逸出幾聲低吟。
「小文的技巧…愈來愈好呢…說的也是,這種事畢竟也做了好幾年…」
紀文閉上眼,把注意力放在那慾望,只想快些解決。
沒多久,紀凜逸出一聲低吼,灼熱滾燙的精華儘射進紀文口中,強烈的腥臭使她的臉皺起來,就要把它吐掉。
紀凜卻緊捏著她的下巴,陰狠地眯著眼:「咽下去。」
紀文攏著眉,鳳眼痛苦地眯著,泛起水霧,在燈光下成了彎水當當的月牙兒。
「小文,妳知道妳現在的樣子有多淫蕩嗎?一副欠操的模樣,嘴都臟了…」紀凜用拇指抹去她嘴角逸出的乳白液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