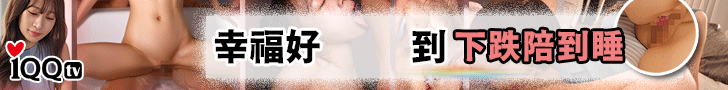台风真的扫过台湾海峡来了,气象局在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钰慧她们出海的计划因此受到阻延,大伙儿困守在饭店里,百般无聊。
尽管澎湖海面彤云密布,恶浪滔天,东台湾却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蜿蜒无际的海岸,碎漫着细白的浪花,阿宾坐在花东线的自强号里,望向窗外壮阔的景致。
假期的关系,车厢里人很多,吵杂纷乱,一些无座的乘客甚至坐到座椅的扶手上,嘉珮因此皱起眉头,干脆斜侧过身体,搂靠着阿宾,以免糟受那些人无礼的压挤。
阿宾昨天送走钰慧之后,回到家里觉得无聊,下午就走去嘉珮那儿想找她相叙。不晓得为著什么原因,那公寓楼下的大门打开了没回锁,阿宾直接爬上四楼敲嘉珮的门,嘉珮还在睡觉,迷迷糊糊拉开门板,看清楚是阿宾,不禁欢欣雀跃地扑进他怀里,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噘嘴抱怨著,怪他这么久都没来瞧她。
阿宾将她高高抱起,她捧著阿宾的脸,啾啾吻个不停。阿宾将她抱到床边,两人叠坐在一起,嘉珮静静的端详着他,然后说:“我好想你啊!”
阿宾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
嘉珮生活在虚情假意之中,意外认识了阿宾这样的普通男孩,一颗寂寞的女儿心,把阿宾当作好朋友多过是当作情人。
阿宾让她窝在他怀里,嘉珮默默地倾听他沉着的心跳声,享受难得的午后温馨。
阿宾喜欢她那头又长又亮的秀发,他用手掌温柔的替她理著,嘉珮仰起头看他好一会儿,突然说:“阿宾,你放暑假了吗?”
“是啊。”
“那你明天有没有空?陪我回家好不好?”嘉珮说。
“台东?”
“嗯。”
阿宾稍微考虑一下,就答应了。
嘉珮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托人替她向店里请了几天假,然后换过衣服,拉着阿宾陪她上百货公司。
阿宾以为她会到女装或化妆品柜去逛,没想到她看都不看,却老在男装部打转,衬衫领带外套皮件,每一样她都详细的询问阿宾的意见,阿宾看她眼中温柔的神采,便问说:“买给家人?”
“我父亲。”嘉珮点点头。
阿宾替她拿主意,选了几件比较稳重的式样,嘉珮摊捧在手上一直看,嘴边儿带着些些的不安,阿宾搂住她的腰,俩人相视而笑。
今天一早,阿宾跟妈妈胡诌了个理由,说要到同学家去玩两三天,妈妈早知道他放假在家里多半关不住,出去走走也免得无聊,只吩咐他路上小心,并没有多问。
阿宾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过街到嘉珮的公寓接她。嘉珮不知道多早就起来整理妥当,已经等在楼下门口,阿宾替她提起好大一只包包,拦了一部Taxi,到台北车站换搭往台东的火车,目的地是鹿野。
嘉珮淡施脂粉,垂到腰间的直发梳得典雅整齐,一件无袖的贴身薄衫半露著可爱的肚脐,短短的窄裙更显出一双美腿是无比的修长婀娜。从上了车开始车厢里的乘客,有意无意地都会不时斜眼来看看她,火车飞快穿驰过一站站的小乡镇,她娴静地将头枕在阿宾肩上,眼睛望向车窗外遥无边际的远方。
阿宾看她长长的睫毛在不住颤动,他搂紧她的腰,轻声问说:“妳害怕?”
嘉珮抿抿嘴,将脸埋进阿宾胸前,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说:“我三年多没回家了。”
阿宾发现她的眼眸里有无数的矛盾。
“你知道吗?那天是母亲节,”嘉珮说:“我没告诉爸爸一声,就走了,一直到现在。”
阿宾在听着,她又说:“我告诉过你,我读的是护专吗?”
阿宾摇摇头。
“我那时快毕业了,像今天一样,我从台北回到家,我以前常常回家的,父亲在几年前因为车祸折断双腿,所以我打算当一个护士,可以自己照顾他。”
“后来妳没当护士?”
嘉珮笑了,笑得那么凄苦。
“我有一个后母。”她说。
嘉珮艰涩的咽了咽口水,阿宾等着她说下去。
“她有一个情夫。”嘉珮又说。
车窗外先前快速移动着的景物在变化,【本文转载自(xx-book.com)】列车就快停入鹿野站了。
“那天,”嘉珮低下头,语调很平静,仿佛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她让他强暴了我。”
可能是火车进站的跳动,阿宾心头如同被巨槌猛猛的重敲了一般,嘉珮仰起脸蛋儿,辛苦的咬紧下唇。
阿宾因为嘉珮的最后一句话而受到震撼,心中忽然万分的痛苦,他几乎忘了他们是怎么走出鹿野车站的,下午东台湾朗朗的阳光,晒得他举起手掌来遮荫。嘉珮在和一辆野鸡出租车讨价还价著,议了老半天,那司机才很不情愿的过来帮他们将行李提去放进后厢,俩人坐上老旧的裕隆柴油车,颠簸地驶出市街。
阿宾和嘉珮一路上都没再交谈,那司机自吹自擂,夸赞自己的开车技术有多棒,飞天钻地无所不能。嘉珮的家还真远,野鸡车在崎岖的山野中开了将近一个半钟头,嘉珮才指引著司机停靠到一条小叉路边,司机又帮他们把行李提下来,嘉珮向他要了车行的电话,说改天回程还要叫他的车,他连忙到车上找了一张名片递给她,嘉珮付过车资,那司机高兴的走了。
阿宾将大包包背到肩上,牵着嘉珮的手,转进小叉路里。嘉珮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小手冰冷,而且在微微发抖,阿宾不住地用双掌帮她搓著,好平稳她的思绪。
就这样大约走了十来分钟,见到前面有两三户散落的人家,一群觅食的土鸡闪躲着他们两个不速之客,咕咕地拍动翅膀快跑,一个妇人和两三个粗壮的小男孩正在手摇水井边洗涤些什么东西,都转头过来,狐疑的看着他们。
“清水婶。”嘉珮喊她。
“啊,妳是..妳是阿珮?”妇人认出她来了。
嘉珮说:“是,我回来了。”
“妳回来了,妳回来了,唉,妳怎么现在才回来..妳..”清水婶叹气说:“回来了就好,妳爸爸在妳们家园子里,妳快去看看他吧。”
“我爸爸在园子里..?”嘉珮犹疑的说。
“小龙,你陪着阿珮姐去。”清水婶吩咐说。
那叫小龙的国中生答应着,走向前去带路。
“在园子里..?”嘉珮又喃喃的唸了一次。
嘉珮当然知道自己家园子怎么走,并不需要小男孩带着去,可是小龙已经抢在前面,嘉珮迟迟徬徨著,直到阿宾低声问她,她才挽著阿宾,跟在小龙后头,顺着泥巴路走去。经过一道小转弯时,嘉珮指给阿宾看,她们家就在不远处,那幢低矮的老房子。
绕过弯路,就已经是嘉珮家的园子,嘉珮神情恍惚,停下来望着园子正中间的农寮,日头赤艳,虫声唧唧,嘉珮忽然觉得脚步像有千万斤般的沉重,小龙转向另一头,招手说:“这边,在这边..”
这一边杂草丛生,咬人猫一颗颗的沾黏住阿宾的裤管和嘉珮的丝袜,小龙在前面停下来,她们俩人跟上去,小龙手指比划处,只见到一邳黄土,上头长著长短参差浓密不均的青草,一门薄薄的石碑立在当前,嘉珮惨白了脸,苦涩的望着碑上的名讳,阴刻的小字记载有日期,表示那是三、四个月前的事,阿宾心里难过,他以为嘉珮要哭了,但是嘉珮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小龙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去了,阿宾放下行李,从背后将嘉珮环腰抱着,嘉珮凝视著小小的土丘,很久很久,才低叹一声,说:“走吧!”
俩人沿着原路,心情沉重地走向嘉珮的家,太阳突然躲进了云层里去,四周变得阴凉许多。阿宾看见小龙和另外两个男孩,在远远地看着他们,交头接耳著。
嘉珮的家里很安静,看来这时没有人在,嘉珮一进大厅,就看见父亲的灵位,她默默的点上三柱香,在灵前膜拜,再把香枝插进炉里,然后拉着阿宾往屋里头走,打开最后头那小小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灰尘的气味,嘉珮望着熟悉的床舖桌椅,这些日子来她虽然不在,小房间一点都没变,她让阿宾将行李放在床上,俩人简单的把室内扫除整理一下,日头已经开始西斜。
嘉珮在冰箱找出一些菜肉材料,到厨房去准备晚餐,阿宾回到客厅坐下来看电视。一会儿之后,门外头响起脚步声,进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中年妇人。
阿宾有点意外,这里的女人多半黝黑粗俗,这妇人却细皮嫩肉,眉目清朗,鼻梁又直又高,嘴唇圆厚,头发半染成紫红,年龄大约四十来岁,身材略略丰肥,穿着干净,长袖丝白衬衫牛仔短裤,雪雪多肉的大腿,脚上登著一双细带凉鞋,趾甲涂著红红的蔻丹,一点乡下人的味道都没有,却有一股俗气的骚劲。
妇人在自己家里突然看见陌生的男人,一时之间有些愕然,站在门边正想问些什么话,正好嘉珮端了一盘菜出来,她更是吃惊,呐呐的说:“小..小珮,妳..妳回来了。”
嘉珮只斜眼看了她一下,放下盘子,自顾自又回到厨房里去了。她有点坐立不安,对着阿宾尴尬的一笑,阿宾回著点点头算是招呼,她考虑了片刻,慌张地跑进嘉珮的隔壁房间里去,关上门,阿宾猜那大概是她和嘉珮父亲的卧房。
嘉珮将做好的饭菜一道道端出来,摆好碗筷汤匙,然后和阿宾一同坐在客厅,边看电视边吃晚餐,那妇人这时才又打开房门,怯怯懦懦走出来。
“小珮..”她说。
“吃饭呐。”嘉珮头抬都不抬。
“小珮..我..”她又说。
“坐下来吃饭。”嘉珮坚持的说。
她只好乖乖的坐到一旁,端起一只空碗,心不在焉的举箸夹菜。她看着嘉珮冷酷的表情,突然感到内心十分恐惧,嘉珮只身在外闯荡,看打扮看举止,显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女孩,她这次回家,有着什么目的?
妇人的一顿饭吃得提心吊胆,好不容易阿宾和嘉珮都放下了碗筷,她连忙主动收拾碟盘残肴,整理桌椅,嘉珮故意坐倚著阿宾不理她,让她去忙得不可开交。
那妇人收拾完成,畏缩地闪过客厅,打算走出门去,嘉珮却喊住她:“妳要去哪里?”
“我..我..我没有..”
“坐到那边去。”嘉珮指著斜角的空椅子。
那妇人垂头丧气,坐到被指定的位置上,电视里正演着乱七八糟的连续剧,她的心情也跟着乱七八糟。她本来想溜出门,去找她的姘头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嘉珮离家之后,她们都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而嘉珮的父亲一过世,更从此将任她们为所欲为,谁知道她突然回来,还带着男人,她不由得心虚恐慌,失去了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