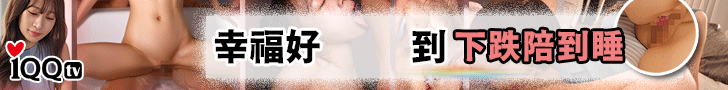這時候,她也披衣走出來,我轉過頭,看見她那張我仿佛無比熟悉又其實從未見過的臉龐,只覺得天旋地轉,腦中飛速掠過諸如時空逆轉、幹坤挪移之類的詞。
她和娃娃實在很像,瘦,長髮,不過她比娃娃略高,沒有娃娃的明媚氣質,卻多一份冷豔驚心的美,眼神中充滿淒愴和淡然。
「娃娃。」三個人之中,她先對娃娃開口了,隨即轉臉對我說:「我叫之偶。」
我完全懵了,之偶不是娃娃已經分手的男友嗎?
娃娃忽然撲進她懷中,大哭起來,「為什麼?為什麼啊?……為什麼你要這麼做?為什麼你丟下我一個人……」
我一下子變成了局外人,矗在門邊,尷尬地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等娃娃哭聲略住,我打開燈,把他們都讓進臥室。
「好了,你們之間總歸要有一個人來告訴我,因為我也想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什麼。」
原來,娃娃和之偶是一對同性戀人,7月份時之偶要求同娃娃分手,並且就此消失不見,娃娃以為她另有新歡,為了忘卻便同我開始交往。但之偶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她發現娃娃是那麼的喜歡小孩,並且也不是天生的P(Les中偏女性角色的一方),本來是可以喜歡一個男人,過上正常家庭生活的。權衡利害後,同時受不了自己無法給娃娃完整家庭的內心壓力,之偶決定獨自走避,希望娃娃可以重新開始。
可是,女人確是一種很難理解的生物——之偶有娃娃的QQ密碼,分手後仍會時常下載她的聊天記錄來看,因此她認識了我,知道娃娃對我很有好感。人在沒有面臨全面的失去時,可以高估自己的意志力,但是她發現娃娃恐怕真的會和我在一起了,終至絕望,做出先於娃娃和我上床之前同我上床的決定,一來拖延我和娃娃相戀的時間,二來加重自己的絕望,堅定必死的決心。
這種自虐的理由在我看來實在荒謬,並且毫無邏輯性,然而對於敏感脆弱的之偶,竟成為一種必然。
我可以解釋為什麼她始終不願意為我口交了,因為Lesbian(女同性戀)是用嘴巴和手指做愛的,對她來說,她的嘴只奉獻給最愛的人。
娃娃這邊就比較簡單,她和我交往只是為了暫緩自己的情緒,確實,她甚至連視頻都不肯,儘管對我印象很好,也沒有變心的念頭。她一直努力找尋之偶的下落,直到最近。
瞭解這一切,我沒有太多驚訝,本來以為自己會憤怒的,甚至也沒有,只覺得心疼,我明白了之偶陰影下的隱憂,明白了她絕望的掙扎,我想起黃碧雲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裡那淡淡的卻撕心裂肺的哀與傷。
我看著娃娃重新找回愛人的喜悅淚光,看著之偶那愈來愈真切、也愈來愈親切的面孔,突然也好想大哭一場。我真的是像自己說過的那樣,努力地愛著她啊,昨天我還想著要堅持這份戀情,用自己的愛擦乾她令人心碎的淚痕,她不僅給了我不同尋常的靈與肉的洗禮,不經意間,也給了我結束浪蕩生活的希望。
「之偶……」我喃喃地念著這個名字,心中五味雜陳,但此時此刻,我惟有冷靜,因為,我是男人。
「之偶,不要再讓你愛的人傷心難過了,娃娃她是個好姑娘。你以為對她好的事,可能成為她終身不幸的罪魁禍首。她是沒有錯的,愛上一個人有錯嗎?至於這個人是男是女,是好是壞,我們有得選擇嗎?愛了就愛了,你不能失去她,她也不能失去你。」
我這樣說著,心底裡也在對自己說,我愛上了一個人,她心裡愛著另一個人,可是,我有得選擇嗎?
「之偶……」我的聲音有些哽咽了,「對自己好一點。」我定了定神,繼續說,「很晚了,我去朋友家打牌,你們就呆在我這兒,好好聊聊,誰都不許再鬧了!」說完我穿上衣服走到門口,之偶跑過來,風一樣輕輕抱住我,在我耳邊一字一頓地說:「不要難過……你是我唯一的男人。」
聽到這句話,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又差點掉下來,我吻了吻她的額頭,示意她回去,然後關上門。哪有心思打牌呢?我去蘇果便利買了一打啤酒,抱到鼓樓廣場,喝著喝著,迷迷糊糊在長凳上過了一夜。
第二天我回到家,她們兩個都不在了,家裡被收拾過了,幹凈整潔,我的睡衣整齊地迭放在床頭。呵呵,這樣子就算道別了吧,我在心裡苦笑著,打開QQ,收到娃娃的流言:謝謝你。隻言片語,不過已經夠了,還能說什麼呢?我該繼續過自己早已習慣的生活。
果然,之後的很久,她的頭像都沒有再亮起來過,我在心裡深深地祝福她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獲得平安喜樂。並且我的放縱也漸次收斂了,家裡繼續操勞著我的婚事,我破天荒地積極去相了幾次親。
12月24號,聖誕前夜,我推掉了所有朋友的邀約,獨自在家趕一個案子,正在焦頭爛額時,酒又告罄,我便打算出門採購,打開門,娃娃正笑盈盈的站在門外,手中一支紅酒遞過來,「哪!給你的,怎麼樣,我很貼心吧?」她不改當初與我聊天時的俏皮神氣。
「你怎麼來了?」我趕緊向門外張望。
「別看了,她沒來。」她吐吐舌頭,「很失望啊?」
「有點,不過你來已經好很多了,平安夜啊,哈哈。」這是實話,也許我愛屋及烏。
「最近是不是繼續放縱啦?爛人?」她進屋,脫掉外套。
我撇撇嘴,苦著臉指著下身說:「什麼啊,你們走後,到現在還沒拆過封呢。」
我打開酒,倒了兩杯拿進來。
她接過來一仰脖子灌下,放下杯子坐到我床上,繼續脫衣服,「那麼今天來拆封吧!」
我嘴裡的酒差點沒噴出來,「怎麼啦?你又發什麼神經啊?之偶呢?」
「我們很好,就要一起去英國了。」她脫到僅剩內衣內褲了,才抬頭微笑著看著我。「我們會在英國結婚,養大我們的孩子。」
「孩子?什麼孩子?」我滿腹狐疑,「你要去人工授精啊?」
「我現在就授!」她撲過來抱住我吻住我的嘴,兩人的舌頭立刻交纏在一起,我私下裡偷偷試著從她的舌尖品嘗之偶的味道,不過確實太久沒有做愛,我的身體很快就被她點燃了。
我一邊和她熱吻,一邊飛快地甩掉身上的衣物,將她壓在身下,她喘息著說:「記住!你的任務是授精!」我不滿地說:「我行啊,你行不行啊?」「我今天是排卵期!」
授精就授精!我剝去她的胸罩和內褲,跪到她腿間,脫掉內褲,胯下怒漲的紅纓槍跳出來時,她俊俏的小臉微微一紅,嘟囔道:「這麼大……」「不算大啦,只是你沒用過別的。」我微笑著開玩笑道,「我這算是被強姦嗎?第一次嘗到被當作生育機器的滋味了。」
娃娃平時和之偶一定性趣多多,而且通常Les都性生活和諧,T(偏男性角色)一般不讓P碰,但對P總是體貼照顧,據說可以百分之百讓P高潮。不過不知道娃娃的處女膜破沒破,沒破還是要受點小罪了。說話間,她的小屄已經濕潤了,我也不浪費時間,龜頭在洞口舔了兩舔,挺槍殺進。
剛沒入龜頭就碰到一點阻礙,果不其然。「你的處女膜還在啊……」我調侃道。
「討厭!你這個生育機器有什麼好囉嗦的……」她臉更紅了,閉上眼睛。
我再不廢話,擰腰刺穿那層障礙,紮入深處。娃娃嚶嚀一聲,剛才因為畏疼而繃緊的身體鬆弛下來。我只覺得她的陰道如同有一個個肉圈連環構成,同之偶一樣,都是緊窄無匹、綿延不絕的上品。我賣力地幹著她的嫩屄,肉棒一下一下帶出處子的落紅,——不,雖然是落紅,但已不能算是處子了吧,我開始幻想著之偶同娃娃做愛的情景,心中好生懷念之偶那充滿韌性的身體。
想著想著,肉棒漲痛得厲害,我加速了抽插,龜頭穿過陰道壁上的皺褶,咕嗞作響。洞內的淫水越聚越多,帶著絲絲血紅,流到潔白的床單上。
「好漲……」娃娃因為心有所屬的緣故吧,一直咬著牙不願呻吟,這會兒終於說話了。
我不答話,把紫脹的陰莖抽離她的身體,示意她翻過身來,屁股對我。她瞪大眼睛,「為什麼要這樣啊?」「沒有見過狗狗交配嗎?你不是要懷孕嗎?這種姿勢才是最自然最適合繁殖的姿勢。」
她再度漲紅了臉,順從地趴到床上,撅起屁股,只見她的菊花蕾上沁透了淫水,一下一下的收縮著,小陰唇顏色略深,微微分開,露出洞口,幾絲黏液掛到精心修剪過的陰毛上,我不禁咽了咽口水,扶正下腹的猛龍,緩緩送入,大力抽插起來。
她依然不肯呻吟一聲,但從她顫抖的身體,我可以感覺到她也在享受這從未經歷過的性愛體驗中。她的陰道一陣一陣收縮,仿佛一雙柔荑般的小手在一下一下握緊我的肉棒。還是第一次同一個性經驗豐富、卻未被破瓜的女人做愛,她不像處女那樣不懂得放鬆與享受,又擁有處女般緊窄瑟縮的陰道,以及從未開墾過的子宮,——想到等會兒還要用我濃稠滾燙的精漿灌滿她的子宮,我愈發覺得刺激了。
我伸手握住她的雙乳揉搓捏弄,她的乳房比之偶大一些,至少是個C+ 吧,渾圓堅挺,乳頭不大,粉粉地硬著。她趴在那裡,尖圓的乳房隨著我的抽插,一晃一晃的,仿佛兩隻成熟的果實任我摘取。
大概因為很久沒有做愛,她的陰道又始終在很有節律的收縮,我前後只抽送了二十來分鍾,就忍受不住了,悶吼一聲,龜頭抵住子宮口,精關大開,億萬個精子噴射出去,爭先恐後湧入子宮。
我正在享受肉棒在她體內跳動的餘韻,忽而背後一熱,兩團熱乎乎的東西貼上來,同時一個人緊緊地抱住我,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竟是朝思暮想的之偶!
確切的說,是朝思暮想的、一絲不掛的之偶……
看到我驚喜地表情,她不禁微笑起來,「做愛都不關門啊,你!」她嗔怪我道,一邊用柔軟的乳房按摩我的後背。我回頭一把將她抱入懷中,再次有大哭的衝動,「之偶!之偶!」我孩子般的叫著,「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她愛憐地撫摸著我的頭髮,說:「這是我們最後的瘋狂了……她家人安排她去英國念書,我也打算過去工作,我們會在那裡結婚了。」
最後的瘋狂……最後的瘋狂!
我差不多瞭解了她們的良苦用心,是了,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我終於相信,她的心裡還是有我的,她們將養育我的骨肉,作為永遠的最美麗的紀念。不要問我為什麼會哭,我恐怕是喜極而泣。
這個世界,還有什麼人能許諾一句永遠?然後我和她,和她們,將經由一種永不能割捨的紐帶,永遠聯繫在一起,彼此,永遠也不能將對方從心上抹去。
之偶和娃娃也都哭了,之偶捶打我的胸口,惡狠狠地邊擦眼淚邊說:「哭什麼啊!哭什麼啊!沒出息的男人,我們是來讓你幹的,不是來看你哭的!」
我如夢初醒般,狂暴地將她撲到在床,讓她側過身子,抱起一條腿在胸前,將紅硬的陰莖狠命插進去,猛力幹她,每幹一下我就想起那時的一個鏡頭:我們變換著各種體位,各種位置,我深情地同她做愛,在黑暗中。她的臉龐從未清晰,她的神情始終有淚痕……
時過境遷,今天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彌補這個遺憾了,我清楚地看到她的每一寸皮膚,甚至每一個毛孔。她的胸那麼白嫩,皮膚幾乎透明,淡青色的靜脈隱約可見,乳頭和乳暈都很小,淺淺的肉色,勃起的乳頭差不多一顆小花生大小。陰蒂幾乎看不出,明顯沒有經過太多刺激,陰唇是嬌嫩的粉紅色,又小又薄,一點沒有變深的跡象,陰毛稀疏,只有陰蒂上方一小撮,娃娃的則經過仔細修剪。
我困獸一般蠻橫地抽插,恨不得把心裡所有的愛怨纏綿都插進她的體內,只見她的蜜洞口一層嬌嫩軟肉被青筋暴起的陰莖帶進帶出,淫水汩汩地順著陰囊淌下來。她死死扯住被頭,在嘴裡咬著,唔唔呻吟,仿佛人已全面沉淪,想把對我的記憶用她的肉體完整記錄下來。
見我如此兇猛地幹著之偶,娃娃已經在旁邊看傻了。僅僅五分鍾,我又要射了,在之偶的花心上輾轉研磨一番後,我迅速拔出突突跳動的紫紅色陰莖,拉過娃娃背對我坐下來,我扶準了肉棒,咕唧一聲順利連根沒入,抓住她重重往下一坐,龜頭再次被她仍然微啟的子宮口牢牢吸住,粘稠灼熱的精液一滴不剩,激射入子宮。
為防精液倒流,確保受孕成功,娃娃趕緊躺到沙發上,高舉兩腿靠著墻。而我整個人都癱軟下來,不僅因為激烈的發洩,還因為心中的頹唐。之偶爬過來,趴在我身上開始吻我。我第一次品嘗到她的香舌,那麼靈活而火熱,霸道地裹挾著我的舌頭,吮吸我的唇齒。我享受著這被動的快感,正欲罷不能,她忽然抽回舌頭,沿著我的胸膛一路吻下去。
我的陰莖軟塌塌地倒在一邊,淫水和精液的混合物粘粘地掛下來,和陰毛纏在一起。她添凈了陰毛和陰莖上的粘液,然後把龜頭含在嘴裡用舌頭挑逗起來,一會兒用舌尖擠壓馬眼,一會兒沿著冠狀溝搜尋,手還不安分地輪流揉搓兩顆睪丸。
到底是科班出身(舌技是Les的必修課),儘管她對於男人的生理構造不甚熟稔,但靈巧嫻熟的舌技,一張一弛、恰到好處的力道,加上我對於她終於肯為我獻出口舌的感動,陰莖很快挺立起來,雖然沒有之前那麼大,依然筋脈交錯,虎虎生威。
這是她便把肉棒整個吞入口中,主動讓龜頭一次又一次頂住喉嚨,不住地吞吐,手溫柔地托著陰囊撫弄睪丸。我最喜歡她吮吸馬眼和冠狀溝,不懂她是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力度的,每一下都是我正好想要的方式,牽動最舒服的那根神經,真是致命的誘惑!
很快,我就再舉白旗,陰莖猛然一震,隨即如火山噴發般劇烈地射精。她趕緊含住龜頭,把精液悉數收納,咕一聲吞下去。
我無力地把她拉上來,抱住她,「之偶,我愛你。」
她溫柔地用臉頰摩擦我的臉頰,「我也愛你。」
……
後來?沒有後來了,愛本來就是沒有後來的事情。
她們至此銷聲匿跡,第二天我在聖誕的落雪中醒過來,想想昨夜,恍若隔世。
上個月,我收到一封來自伯明罕的信件,只有一張照片,那是大腹便便的娃娃在幸福地微笑。之偶?我知道她,她並非沒有給我任何訊息,從娃娃的微笑上我就能明白,鏡頭後的人便是之偶。
至於我,幾乎已經和以往的浪蕩生涯一刀兩斷了,我下定決心,因著我那未知的嬰孩的緣故,因著我命運中怒放的兩生花,從今以後,溫暖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