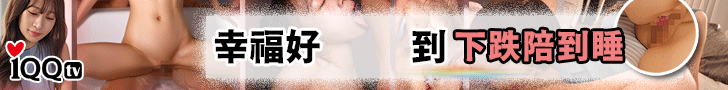我抬頭示意輝接續我的位置,我將身讓開,用嘴吸吮她的乳,乳紅漲得如粉大的小荔枝核,漂亮地崛立著,我一含弄,她便喘息,而手卻是順著我的身去向下找尋她急要的物體,我把身子往後賴著,她終是夠摸不到。輝到了我的位置摸到她的腿準備分得更大,妻子被他的手一摸兩條腿頓時象受驚的河蚌攏在一起,我用一隻手配合著輝把妻子的腿慢慢分開,妻子的腿有些微用力地閉著,不過已經從交疊著開始被我們分開了一些,我們慢慢分開她的腿,感覺出她的抗力越來越小。
我急不可待地想實現我的願望,我一隻手從她身下透過溫柔地攬著她,再把手指重再深入她的身體,妻子的腿立時夾住我的膀子,然後又被我們輕輕分開。
輝已經急不可待,堅硬的陰莖陣陣彈搏,他對鼻子下的肉體窺視已久,見妻子的腿間露出空擋,他立時乘隙前傾,陰莖立時頂在妻子穴口的毛溪處,她的腿一下子受驚攏起卻正好夾在了輝粗的腰上,我慢慢退抽出手指,妻子的腿一點抗力都沒有了,軟軟地分搭下來,只是臀在輝的身下左右不住地微扭,看得出她理智的抗拒和身體慾念的渴望在激烈地交斗。
輝起了一些身,就著燈光找尋妻穴的準確入口,微扭中穴口的陰唇隨著左右而微錯,內中若隱若現的穴眼越發顯出一種叫人急於進入的誘惑。輝喘著粗氣,在妻子的扭擺中手攥著自己糙粗的陰莖向下迫著將黑油甑亮的龜頭頂住微微擠開的妻子紅緋的陰唇間,妻子好像夢醒了一般,扭動得更厲害,輝緊緊用力按壓住她的腰腿,不讓自己的陰莖從她的陰道口落開,我將唇罩在妻子的唇上,用舌頂入舔吮著妻子的舌,輝身體沉重的一股向下壓力從妻子的那端傳過來,妻子悶哼了一聲,下身強力扭擺了一下,不再動彈,一下子吸裹住我的舌。我沒回頭看,但是知道輝終於如願以償,那粗大陰莖猶如戰場渾實瓚亮的潛艇沒入了妻子密穴之中。
我用手卡在他們之間,怕輝碩長的陰莖使得妻子承受不了,不敢讓他全部進去,輝那堅硬陽物的質感從我手的觸感傳來,它現在硬鋌而勃發的擠迫在妻子蜜柔的穴內,讓我不由得對妻子的身體被這個陌生男人的佔領感到一絲心痛。
之前我是滿心希望,之中我卻是酸楚而復悔,但我還是慢慢抽離開手,終於看到輝的莖根密實地擠頂在妻子的穴上,那天在酒店衛生間裡見到的濃密多盛並油亮的那些陰毛的影子,今天真實交蓋在妻子娑小微卷的穴毛上。輝將自己的身體緩緩地再抽離開去,直至全部退出。
妻子攬在我背上的一隻手開始甦醒似地輕輕擁拉我,我沒想到妻子這麼快的可以適應,我甚至以為剛才的一瞬間妻子會被輝急速闖入的粗實東西擠脹撕扯得喊叫出來,但是看來她是接受了。我也知道那一瞬間使她無法把輝的侵入和海東的進入聯想在一起,輝是急切地帶著野蠻地給予她的是一個全新的男人性器進入她的身體,而中呢?我無法想像,也許是溫柔、多情、纏綿,而我卻希望輝的這種野蠻的力度能在她的身體深處留下重度的印記,而這個印記最好能全部覆蓋住海東給她留下的感覺!
我希望她現在的思想和她的身體一樣,開始渴望起這個她先前牴觸的男人。
也許只是暫時,但是這一時刻,她是願意被進入了的。輝十分在意他的動作的輕重,插入的深淺,似乎男人對侵入一個陌生女人的體內,也是非常地想尋思個究竟,就如之前的理工大的那個學生和他的同學,濟南的那個男人,凡是有我在場的,他們都在意。
我之前和輝說了很多妻子的喜好,他在這時便融會其中,我跟他說我每次只要拚命地插到底,是可以感覺到妻子裡面最深處一個小口的緊密,應該是所謂的宮頸,但是我卻是插不過去,我撩撥他,說如此長的陰莖一定能頂過去,他在現在卻是很想親身體會這個結果。
但是很深的時候,老婆就有些受不了了,用手卡在陰道口,不讓他太進,輝於是便不再猛烈,而是翻過妻子的身子,妻子聽話地翻過來,枕巾掉下來,她只是閉著眼睛,這是她的習慣。兩個奶垂蕩在伏起的身下,大而白。
輝重新頂入妻那被他插得已經開放很大的陰道口,應該是捅更合適些,我真正地開始心痛起來,輝的動作猛烈得叫我膛目,我後悔和輝一起時為了報復妻子對他說妻子喜歡很猛烈地插她的話。輝開始用後進來抽插,我在他們身後,他起勁地推搖著妻子的臀或動靜著自己的腰,兩顆大懸的睾丸也隨身擺動。
我熱血沸騰,我發覺這個時候寧願自己是旁觀者,這場景如是隔壁看院的蠻夫和府中難抑春情而偷的府眷。在他們的交合處,妻子微翻如孩童生氣噘起小嘴般的陰唇緊緊密實地吸吮包裹著輝全貫而入的黑的莖柱。他的睾丸緊緊貼在莖根上,但露出的一小截根讓我還可以看到那正鼓漲的尿道的凸起。
妻子估計被輝抽插捅弄得開始舒適,也習慣輝這樣猛烈而少溫柔的動作,到輝間隙微停的時候,她也會不自禁地扭動自己的腰臀來向輝反映自己的需要。輝黑雍的腿矗在妻子白花的腿間,使我想起了北京劉斌那次和妻子的激戰,也是這樣的姿勢,男人戰鬥時的姿勢似乎都比較相似,只是從妻子臀股間出現的汗毛濃重的雙腿,或者是黑雍粗壯的雙腿來感覺這些不同個體的男人。
我沒有忘記還有一件事情要做,把枕頭下的保險套拿出,輝抽拔出自己的身體,將套膜撕掉,認真地套在陰莖上,保險套被繃得拉緊,下端只能套在陰莖的三分之二處,我著實驚訝於他的碩大,不過很快,他那蒙上膠膜的陰莖又湮沒在妻子身體下端的陰影裡。
輝結實和密集地捅插了妻子足足有半個多小時,臉上身上都是汗水,最後時刻駭人的力度撞擊得妻子的臀響起很大的他們之間肉擊的劈啪聲,妻子的陰道完全被他插得鬆開,輝的插入最後基本就是直進直出,他甚至可以不用看妻子的下口,就直接將完全退出的陽物筆直地衝進她的身體裡,妻子的頭髮散亂不堪,安利沐浴露的味道被她極高的體溫熏炙而在臥室的空氣裡流散,與我和輝的汗味交混在一起,生出一種怪異叫人癲狂的氣味。
幾次中妻子被輝擊撞得倒伏下身子,輝又攬起她,並並緊她的雙腿,我把陰莖給妻子含住,但在她後面猛烈地被撞擊中,因喘息而不斷吐出,我只能在心裡期望輝盡快地射出結束,我已經心疼到極點,底下也已經疲軟。輝半蹲起來,架在妻子的臀上用了一個高位置,腰狠狠地來了個前頂,用手壓住妻子的脖頸迎著自己向後一按,隨後緊緊抓住妻子的乳,嘴裡沉沉地低吼著,深深入進而不再動彈。
妻子吐出我已經軟去的陰莖,閉著眼睛,手抓在輝按在她乳房上的手上,一動不動,承受著身後男人原始的釋放。輝壓蹲在妻子的臀上,腿半曲著,他的臀肌還在收縮著。然後又抱伏在妻子的身上,臉貼在妻子的背上。只有下處還在輕微地動扭幾下。
於安靜中,臥室裡的那種感覺也在急速地沉澱,平靜下來的輝,抬起頭望著我,又看了看妻子,妻子依然前趴在他身下,沒有動彈,我沒有任何表示也沒有什麼表情。妻子的臉被凌亂的頭髮蓋著,輝往後開始試著退出,和妻子身體分開了一些,他便用手探下夾住保險套的端,而後慢慢抽離出妻子的身體。他還沒疲軟掉的黑雍陰莖上,皺曲的保險套前端汪滿了乳白色的漿,多到溢滿到小套的上端,如果沒有這個膠膜的束縛,妻子的陰道里這時應該充滿了輝的精液。
她那空洞腫脹的陰道口,沒有往日男人的溢出物好像顯得有一絲荒涼,越發使我感覺到輝這個傢伙開墾妻子的蠻道和無情。其實他就是來遊戲一次的,本來就沒有任何感情色彩在裡面,這個男人就是為了那最後的十幾秒從一個城市顛沛到另一個城市,無非是為了將自己積蓄時日,憋漲的生理物質和精神探奇一起排泄在稱之為我妻子的女人體內。
對我來說,我真的很喜歡這樣的遊戲,甚至精神的大於肉體的。對於妻子來言,我也希望她每次皆能快樂到及至,做一個能徹底投入其中去的女人。那些在她身體上起起伏伏的男人們只把他們看作是一個個可以動作的性歡工具好了,他們可以給我帶來視覺的高度刺激,可以給我們的身心帶來極越沖頂的高度。
想得漸多,我又開始膨脹起來,起身上去,將苦熬半天的陽具插入老婆的身體。書上說女人的陰道有很大的適應性,我感覺到剛剛被輝大而粗的東西開墾過的妻子的穴,確是空鬆一些,於從前和他人一起過是沒有的,不過我向來喜歡鬆一些的穴,感覺不會洩射得很快。
在我的抽插中,我一陣陣地刺激妻子的陰道上端,妻子沒有往日的迎合,也沒有什麼大的反應,我開始感到索然,很快地就想結束,最後我一洩如注,妻子也筋疲力盡地躺在床上,我抱著她問她:「舒服嗎?」妻子不說話,很虛弱地看著我,閉著眼睛,這是唯一的一次看妻子被人抽插得如此出勁。
結束後輝去洗澡,我和妻子都沒說話,我只是摟著她,她偎在我懷裡像只受傷的小貓,等輝向我打招呼回書房睡覺後,妻子去衛生間梳理,半天沒聲音。我輕輕推開一個小縫,妻子坐在便器上,神情黯然,低頭用手撫弄著自己的陰唇。
我進去蹲在她面前,分開她的腿,破散如敗落花瓣似的唇緣紅腫不堪,向外翻突著,然後她閉著眼睛等待著什麼,「譁」她唇間灑出一股清黃的熱尿,這其中,她皺著眉頭,好像有疼痛感。完畢,我忙遞給她軟紙巾,她拭的時候很輕很輕,而後起來洗澡回臥室,我們一直無話。
早上輝又摸到臥室裡,擺弄起妻子的身體,妻子極力反對,輝無奈,我也示意他不要再試圖進入妻子,輝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引得妻子這樣對他,但還是停下,躺在妻子的身邊。我抓住妻子的手按在輝多毛的小腹下挺立高高的陰莖上,妻子只是按著或者握著,不動也不拿回。
我讓輝把身子上挪,將陰莖停在她嘴邊,然後在她嘴邊輕輕的往裡送,妻子慢慢地張開嘴,輝小心地送進去,一點點一點點地伸進去,只進到一小半,妻子的喉就開始反射性地嘔,輝忙抽出來,又指指妻子的肛門,我連忙搖頭。最後輝開始自己套弄,在最後快射出的時候,我正過妻子的身子,輝伏在她的臉上,將精液射進妻子張開的嘴裡,妻子只被他飆射進幾下,就連忙爬起,拿起一條枕巾掩住自己的胸直奔衛生間,而後是嘩嘩的嘔吐聲。
我讓輝回書房早點休息或者回濟南。中午電話妻子說,小腹墜漲得緊,不知道是不是這次過了,後來還是老說有墜漲感,我帶她去醫院,醫生檢查後說,沒什麼,宮頸輕度糜爛,用泡騰片治療,注意夫妻生活。
晚上我們也沒大說話,我在QQ上遇見輝,問他:「怎麼樣?」他說:「很好啊,就是早上不知道怎麼了?」我說:「你嫂子那裡給你整得很疼,你怎麼也不輕點?」
輝說:「是哥你叫我猛點啊。」他女朋友就受不了他的大雞巴,一般他只插一大半,不敢很深的插,他就是總也感覺不到過癮。和我們這次他非常高興,下次要是不帶套,就更舒服了,還問我:「看你文章知道哥喜歡別的男人射進嫂子裡面,我不可以嗎?」我心想希望有可能下次吧,他自揚地說:「哥我是不是很強啊?」
我在屏幕這頭無心聊下去,推說自己要下,其實我想和妻子談談。
妻子在看電視,情緒好很多,我試探地和她說話,說遇見輝了,問嫂子好,她就是「哦」地回答我。
我問:「這次有感覺嗎?」
她說:「沒感覺,對他本人也沒感覺,不是給你面子第一次也不可能。」
我見她和我交流了,知道妻子沒什麼心氣了,便繼續好言輕語的問:「他的東西大吧?你怎麼受得了的?」
妻子說:「是夠大,其實一開始就不想和他做,你還幫他讓他插我,我後來也不想拒絕了,拒絕也沒什麼意思,就讓他進去了。」
「什麼感覺啊?」
「大,很大,剛進漲得我受不了,我是屏住氣讓他頂進來的。」
「進去是不是就舒服了?」
「不是做愛的舒服,是漲得舒服,他抽刮得讓我感覺他的下面像個大吸管,一抽走,我就有空的感覺,像給什麼掏空了肚子。」
「後來呢?」
「後來沒知覺了,只是知道他在插,不停地動,到後來他用力的時候,我裡面又酸又痛,我是摁著肚子的,你沒看見嗎,他從後面的時候,感覺被他刺穿陰道了,最裡面忽然一酸就鬆開了,就感覺他的前面鑽進子宮裡了,然後是痛,我就往後退,他摟住我腰往他身上帶,後來我都沒快感了,就像被人強姦一樣,我看被強姦就是這個滋味了,裡面很乾,火辣辣的,帶著套更干,我很難受,也沒水了。」
「那就沒一點有想頭的地方?」
「要說有就是那種刺激倒是沒有過,和別人也沒有過,現在想那些片子裡的老外女人被那些男人狠命地插,她能受得了嗎?不被插死才怪,我是領教了,還這麼大,想想都後怕。」
「你不是也挺過來了嗎?看你中間還挺快活的,看你還直扭,呵呵!」
「我幹嗎不快樂,你看著快樂,我再不要舒服,我不虧啊,我再問你,你看著這樣男人弄你妻子,你真的舒服嗎?」
我心裡咯?一下,她的話有點問得不尋常,我還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我於是連忙解釋:「我是很舒服啊,看你被別人愛,我很高興,起碼我妻子被這麼多人喜歡我能不姿嗎?要是你上街都沒男人看你一眼,你活得可憐不?」
「可是這不像是愛,我好像成了你的一個工具,就是滿足你某種慾望,我不知道這種慾望是不是正常,但是起碼在大多數人裡面是你這個心態有問題。」
我們第一次談到這麼深,我一直不想探究的自己的實質卻被妻子幾句話而打開了問題的匣蓋,但我確實只是喜歡這種酸楚,痛苦與激越亢揚交替和摻雜的感覺,而這個感覺只有在妻子被陌生男人插進身體的一瞬間成為起點,在他們將自己的精物盡數洩排進妻子的陰道里而達到高潮。
我最迷戀妻子的陰門被別的男人插得微翻的樣子,看別的男人在妻子身上激烈地起伏著?。我渴望妻子能理解,而因此我們可以更好地溝通,但是現在看來出了一些小問題,我在尋找這個問題產生於何處或者根源在哪裡?是妻子和海東的感情已經開始讓她迷戀於這個人高於對她身體交歡快樂的程度?或者因對海東的專注而對別的男人開始牴觸?
我把對這個事情的感覺和自己的想法原本地向妻子說出來,我認真的表情讓她開始咧開白白的牙笑:「好了,這又不是學術研討會,只是我有些奇怪罷了,以前也沒注意到,只當是夫妻生活的一種新方式吧,不過這種我不順眼的男人真的我不喜歡,我當時怎麼叫讓他插進來的呢?現在除了能想起他很大,很漲的感覺,他長什麼樣我都記不得了。」
說到這個事情,我又不由自主地勃動起來,剛才的反思已經不知道忘到哪裡去了,腦子裡竟然又冒出讓輝插妻子的想法,不過我沒敢說出來,而妻子摸著我硬邦邦的弟弟,嬌笑著說:「是不是又想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啦?要真想,讓海東來吧。」
一提到海東,我的某種單純的慾望更加強烈,但是想到他那副嘴臉,雖然謙笑著,但是我感覺咋就那麼陰險呢?妻子怎麼就喜歡這種大白臉呢?像抹了白灰的戲台上的魏忠賢。
想歸想,但是還是沒忘了剝開妻子的衣吸住妻子的乳,三下二下就和妻子滾在一起,沒了別的男人一起的前戲雖有些索然,但是看來妻子是快樂的,我們在愛中快樂地嬉戲,為了讓妻子衝擊得更高,我仔細描繪著海東怎麼怎麼來操她,老婆很快地衝上峰頂,一波又一波。
(十六)
輝品髓知味,一個星期後自己又來了。這次很麻煩,我怕傷心他,對輝說:「你嫂子好像和你不是太舒服。」輝反問我:「那嫂子那天看著很姿啊,這次我會溫柔對她,大哥,你看行嗎?」
其實心裡我真想讓妻子被他再來一次,因為和輝的視感是最刺激的,想到輝那碩大的陰莖一點點擠迫進妻子的穴的樣子,我就激盪起來。我在興奮中,於是便想再把輝帶回家,我知道如果我非做不可,妻子也會同意,但是我也不想勉強妻子太過,我想了個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