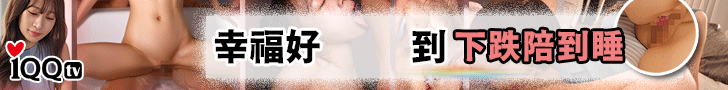剛見到她是在上海火車站附近,那是一九九四年春天。
老闆派我到上海參加一個幾年一度的電子展覽會,白天在會展裡逛了一天,傍晚匆忙趕到火車站買票打算當晚回杭州,不料最近一列客車要到晚上十一點才有。現在才七點,住宿一晚,顯然不是老闆所願意的,怎麼辦?
在廣場上四處茫然,遠處幾個腥紅大字歪歪扭扭地寫在一塊搖晃的招牌上:「豪華大巴,發往杭州,蕭山」。
就在我排隊上車時,看到了她,準確的說是她的背部。她就排在我前面,短髮,淺黃色的上衣,背著帆布旅行袋,憑我的經驗,她大致是那種在外地闖蕩的頗有經歷的鄉下女孩,因為在這樣的長途汽車上,只有她們才有膽量一個人獨來獨行。不管怎樣,在漫長無聊的旅途中,如果能跟她聊聊侃侃,也是一種打發時間的好方法。
「你上哪兒?」
「蕭山。」她轉過臉來朝我笑笑。模樣還不錯,我來勁頭了。
上了車,我幫她找到空位,當然條件是要我們坐在一起。
我開始找話題聊天,記不清具體吹些啥。大學四年的寒暑假來回旅行生活,使我對付這種場合駕輕就熟,讓一位女孩從見面到熟悉,到哄她開心,到留下聯繫電話地址,真是a piece of cake。
她剛開始只是睜大眼睛默默的聽,後來吃吃的笑,然後她的話也多起來了,她說到上海是要找她的中國一個小姐妹。
「她在哪兒?」
「在新莊,不知道具體地址。」
「那怎麼找她?」
「我僱了摩托車,四十塊,讓他帶我四處找。」
「那你找到她沒有?」
「沒有,所以先回去,你看這麼晚了,回家要半夜了。」
汽車開到閔行,不遠處一群建築樓的燈光在暮色中顯得格外顯眼,四年過去了,我還是能馬上分辨出哪是「教三」,哪是「行政樓」。
我指著那邊說:「我在那兒讀書住了兩年,那個時候真好,整天瞎玩。」
「你怎麼玩?」她笑著看著我。
「我有一把破吉它,彈彈琴,週六晚上我們就跳舞去,老踩別人的腳……」
她的目光移到遠處,在想些什麼,在暗淡的車燈下,我可以看出她幽幽的眼神。她見我注視著她,忙說:「怎麼不說了?」頓了頓,對我說:「可惜我沒機會去大學讀書。」
我安慰她,【本文轉載自(xx-book.com)】又聊了一陣。不知不覺已到了深夜,我迷迷糊糊靠在座位上睡著了。我感到車子似乎在慢慢傾斜,有人在旁邊急急的推我。司機說:「大家不要動,不要緊張,右邊的先下去。」
原來車子偏離了路面,右邊的輪子已經陷在路基外側,車子嚴重傾斜。我拉著她慌慌張張地跑下車,外面一團漆黑,只聽到窪蟲在水田中的叫聲。一陣風吹來,我打了個哆嗦。她也緊緊的裹牢外衣,雙手抱胸,看她這個樣子,我只好脫下西裝,披在她身上。
「你自己穿吧,你不要凍著了。」
「我不冷,沒關係的。」我咬咬牙。
大約過了半小時,另一輛客車開到,大家一片歡呼,爭先恐後上車,我們在最後,不知有沒有座位。上了車,前排有兩個隔開的位子,最後一排也有兩個位子,她徑直地走向後排。我樂了,看來她喜歡跟我坐一起,因為後排很震,一般沒人願意坐。
這段路正在施工中,車子搖搖晃晃地前進,我們的身體跟著左右搖擺,我不經意地撞到了她,慌忙平衡住自己的身子,一剎那間,感覺到了那少女特有的柔軟和彈性。她也搖搖晃晃地碰撞著我,慢慢地,我們不在刻意避開。
終於,汽車離開了施工路段,但我們卻靠得更緊了,她把頭靜靜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們沒有說話。
十二點半,到達了杭州。我走下車門,看著車門後面的她正在猶豫要不要下車,我知道她到蕭山後仍要轉車,現在這個時候,那邊不一定有車子,而且那兒找旅館也不方便。
我們目光相接的一瞬,我突然覺得在這茫茫的黑夜應該幫幫這個孤零零的女孩,對她說:「你明天再從杭州出發吧。」我幫她拿下那隻旅行袋,叫了一輛的士,開往花園殿。
我沒有自己的房子,公司在花園殿為我們租了兩間農民房,我一人住樓下一間。我帶著她在黑暗的小巷中走,深夜沒有一點聲音,我在前面帶路,不停的回頭看她,真擔心她是否害怕,她「噗嗤」一下笑了:「你是不是怕我走丟了?」我心中坦然:「是啊。」
帶她進房,指著那張床對她說:「你就睡這兒吧。」她看著房中的傢俱,一張單人床、一張破桌、一把方凳、一台燈,愣了愣,說:「我以為至少有長沙發之類的。」
我說:「不要緊的,我今天晚上要看書,看通宵,你就睡床上,沒事的。」
我打開台燈,拿一本那時以為很牛的書——AT命令集,認真地看了起來。她默默的脫下外套,躺在床上,蓋上被子。或許她太累了,沒過兩分鐘,就響起輕微的鼾聲。我看著她熟睡的臉,不禁為自己的騎士精神和紳士風度而感動。
看了半小時的書,兩眼發昏,正想強打精神,忽然聽她說:「你也睡吧。」
「我不睡,沒事。」
「可你開著燈,人家睡不著。」
看著燈下她微開著的雙眼,我不禁心中砰然一動:「我睡哪一頭?」
「隨你。」她說。
「我腳沒洗,看來只能與你同一頭了。」
她笑著說:「我也沒洗,沒地方洗。」
我戰戰競競地挨著她半躺下來,關了燈,頭靠在牆上,全身發燙,下面膨脹起來。
我說:「我怕剋制不住,這樣對不住我女朋友。不行,我得起來。」
她倒顯得很平靜:「其實沒事的,我們都有自己的男女朋友,就算我願意好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或許潛意識中正等她這句話。黑暗中,我的右手輕輕的摸索著她的臉龐。我的下部熱脹難受,她的呼吸也急促了。她抓過我的右手,放在她的胸脯上,我再也把持不住了,一翻身壓在她身上,她急切地迎合上來,雙手抱緊我,臀部不停的向上挺動,口中含混不清的說:「我要,我要……」
同時她雙手轉到下面,嘗試給我接開皮帶,對,是皮帶,我也迫不及待要解下她的長褲,雖然我壓著她,但並不影響我們順利快速地解開褲子。當我們把長褲連同內褲拉到膝蓋處時,等不及全部脫下,我已急急忙忙往前一頂,她喉嚨裡「啊」的一聲,閉上眼睛,我進入了她的身體,我第一次感覺到裡面的柔滑、彈性,和熱度。
這是我第一次完全進入女人的身體,我有時也與女朋友玩得很火,不過最多是在外部撞擊一番,我們一是怕懷孕,二是怕把她的膜弄破,我逃脫不了責任,最後總是我把精液流在她的外陰,然後她從容地把它擦掉。
我從沒見過女友像她這樣陶醉在其中,她閉著雙眼,每次我往前送時,她喉嚨裡發出輕微的「啊」的一聲,同時抬起臀部往上迎合。抽送了五、六下,我已經感覺下面快控制不住了,連忙拔了出來,對她說:「我們把衣服全脫了吧!」
解除掉所有的障礙,我又開始壓在她上面開始抽送,這一次我們赤身裸體,更加感到刺激。抽送了十幾下,終於精門一動,我下面無法控制地痙攣,陽精一陣一陣地噴射到她的花心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