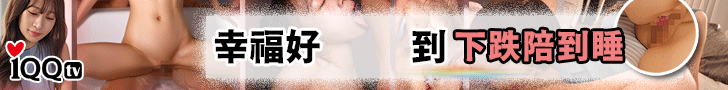性欲毕竟是人的欲望中最强烈、最难被压迫下去的一种需要。它一旦被调遣起来,就强大的不得了。而女人的潜意识里都有受虐倾向,都喜欢男人半强迫的像凶狮一样威猛。
娴自己都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变得有点淫荡起来。她不由得鄙视起自己来,又有点恨自己。她在心里数落着自己:”我怎么变得这么厚颜,没出息。”
人的生理需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有所不同的。男人是二十多岁性欲强,到四十多岁就逐渐减弱了;而女人则正相反。她二十多岁时,性欲主要是他男人的事。她第一一次不知不觉地做了大家都知道的很辛苦的事,由于条件的限制,是站着的姿势完成的,没有太多的感觉。几年来,自己将近四十岁时,她对性的要求非常强烈,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生理和心理的第二个青春期吧?难关她看到不少中年饥渴的女人,目光贪婪地在男人们的裤裆间游走,那神情就象在挑选一匹健壮的牲口。
娴正处在虎狼之年,精力旺盛,渴望得到男人的爱抚。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有权力得到生理上的满足,可是偏偏常得不到。娴想:可能是自己长期得不到男性的爱抚,遭受性压抑,才产生这种变态的幻想,才幻想着被刚才那个男人强暴了,欲望能使人变成这般,自己仿佛都不认识自己了,真是不可思议。自己是一个好女人,怎么有这种坏想法…想到这,娴惊醒了,她不由得哭了起来。
她还年轻,还有希望,这种日子,她不想继续下去了,否则,她会垮掉的,她要振作起来,她要战胜自己,重新赢得爱。
为什么要束缚自己,把自己变得这样的自卑啊!你就不会像现代女人那样敢爱敢恨,轻轻松松地表白自己,轻轻松松地活着,非得套上枷锁。娴用坚硬的拳头捶着床,一直捶到她发现自己已经是在流泪。她感觉到冰冷的泪顺着脸颊往下蠕动。
她抱着双臂,从未有过的寒冷袭击了过来。她往上拉了拉被子,把头往里缩了缩。
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雨,仿佛这雨是为了安慰她的孤单而特地出现的。雨点是那么小,却又是这般多,多得使她再度涌出泪水。如果世界遗弃了她,至少雨不会。
她的喉头一阵哽咽,温热的东酉冒了上来,她开始更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哭声。带着绝望,也带着感激。
娴想:”我要是找到爱我的他,我会用心去体会这份真情…”她睡下又爬起,爬起又睡下,反反复复朦朦胧胧直到深夜。
天快要亮了。娴仍就这么胡思乱想着,虽觉得疲劳,但大脑却持续兴奋,又累又睡不着。那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感觉。
第2章
初夏的一天,生活新的一篇要开始了。
娴和一位元在单位认识多年,却没有深交的男同事垙一块开会的时候,偶然地把座位排在了一起。娴和垙听报告听得无聊,就一会儿写纸条,一会儿发信息,或说俏皮话,或谈正经事。最后,两个人互相比年龄,垙说自己比娴大,娴说自己比垙大。再后来决定,以身份证为证,谁小谁请客,到茶吧去唱卡拉OK。
结果呢,娴输了。
吃过晚饭,娴信守自己的诺言,邀垙出外唱歌,还很慷慨地愿意请几位漂亮的小姐陪垙。垙欣然前往,却拒绝了小姐们的作陪的想法。
一对孤男寡女来到了他清静的汽车里。
娴一开始就感到不自在。毕竟是和异性单独相处,而且挨得那么近,两个人就这么坐着,中间隔着窄窄的一条缝。要知道,娴并不是放荡不羁,轻浮的女流之辈啊?尽管不自在,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说不出来。
她喜欢垙这样的男人,高挑的个子,很儒雅的风度,是一位白领的绅士,成熟沉稳,教养当然没有说的。他那天的穿着很潇洒,一件蓝格子衬衫配了一条浅色的金利来领带,外衣是一件皮尔卡丹西装。他高高的身材,他的五官就像用刀刻出来的,比例匀称,弧度优美,脸上洋溢着温文尔雅的神态。嘴角扬起一丝迷人的笑容,如同从画面走出的肖像那般。绸缎似的肌肤,平滑有光泽,虽稍嫌微黄,却不影响雍容华贵的气质。他的眼神露出一抹锐利的光芒,想必他对自己的气质和容貌充满了自信和满意,不时地溢于言表,他的周身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贵族般的气息及骨子里深藏着的狂傲。这气质不是装模作样就能做得到的,也不是能够速成的,它是一个家族几代风范的结晶。娴悄悄地打量着他,又高又帅,周身上下凭添了浑然天成的风流气息,举止潇洒,这男人生来就是要勾引女人的,自己难保不会为他所倾倒。
不知什么时候,垙将将身体靠近娴,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他属于健壮类型。他涨股的肌肉,无声地引诱着她。这时候,她常发现垙在看她和她的乳房,带着不是那么纯洁的、也许是有点罪恶眼光。她知道,在这闷热的夏日里,她穿着白色的方领无袖衫,双臂裸露在外,胸部虽没露出乳头的形状,但透出奶罩下饱满的乳房对男人的引力。她看见了他那幽冥般的炯炯目光,飘浮不定。这双咄咄逼人的目光在她脸上、胸脯上放肆地烙著,似乎已扒光了自己的衣服。她从垙的眼中看出了他的贼心:对她身体的贪婪;她也闻到了他那男人情欲高涨的气息。
垙知道如何一点点地点燃娴的火焰。他不但有个贼心,还有一个大贼胆。他渐渐地把他和她的手握在了一起,娴竟并不感到特别的陌生;垙和娴的头也就不由自主地靠在了一起,竟不感到羞涩;垙突然将娴相拥在一起,激情的热吻,像已奔放的潮水,两张涨红的脸,一阵阵急促的呼吸。
当垙触摸到娴的大腿时,没有受到抵抗,他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麻利的左手钻入了几乎只能围住娴股部的裙中,右手揽住娴的腰际猛烈地将她拥入怀里;进而他把娴的无袖圆领衫象块布片一样搭在她高耸的乳峰上,解开她的乳罩,将他的胸部紧压住她的乳房,娴的唇角正微扬起迎到面前,他们的鼻尖没有相触但却感到了对方的热度。垙片刻地注视了这张双眼微闭着的脸庞,精致生动而美丽,他不是在吻它,而是试图一口将其吞入然后咀嚼。
这时,她感觉到了一个热热的、硬硬的”贼”东西接触到了她的大腿,啊了一声,手却不知不觉伸向了它,就在手指刚刚触摸到它的那一刻,又缩了回去,她不知道他那裤子里的东西是特号的。她惊叫一声,挣脱他热而湿的嘴唇,叫道:”不,不可以这样!天哪,你是属驴的,还是属马的,家伙怎么这么大!”她这辈子就只体会过她丈夫的中小号,然而她的身子被他圈得纹丝不动。
垙攀抱着她,他的手早就象蛇一样地下去了,裙子太紧,他的手急得只在裙腰上抓,把裙扣在后边解了,于是那手就钻进去,顺着娴的裙带向下不断寻,在下面摸搓开来。他抱着、吻著、摸著…找到娴的好感觉,摸到了湿淋淋的一片。
娴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垙的两只熟练手。她在这个男人的拥抱和抚摸中开始一点一点地缩小,她不动弹,也不想动弹,她愿意就这么缩小下去,直到自己化了,没了。她的身躯开始降服地瘫软下来…娴开始清醒地明白当今新一代的理论:别抵抗你无法控制的事,面对你别无选择又无法逃避的欲!
垙把软得如面条的娴放倒,开始把短裙剥去,连筒丝袜就一下子脱到了膝盖弯。他的感觉里,那像是剥一根葱,白生生的肉体就赤裸在他面前。他手从她后背伸进内衣,触碰到乳罩的扣子,两根手指从扣子两侧挤了一下,扣子就开了。他另一只手也伸了进去,两手一前一后地上下地抚摸着她那光滑的后背和她丰满肉感的乳房。他又脱下了她的衣服、乳罩,她赤裸的胴体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两手握满她丰腴赤裸的肉体,温柔地抚摸着她丰满肉感的乳房,手指抚弄她的乳峰…他的冲动在变得很坚硬…性兴奋也使娴失去了理智,她知道,这最后一道防线,两个人都恐怕是守不住了。她颤抖地抬起臀部,不自主的为他的身体展开,他毫不迟疑地迅速移到她的身上。
她想说别那么冲动,可嘴已经被他灼热的唇给封死了。她开始本能地、但很微不足道地挣扎,手推着他颤抖的身体。他不管,一边亲吻,一边粗暴的扯下她身上仅存的三角裤。
娴有一点害怕起来,她只觉得她裸露的身子被他紧抱着,等待着他的来势。她心里面的什么东西在抖战起来,而她的精神里面,有什么东西僵结起来准备反抗,反抗这可怕的肉体的亲密,反抗他的迅疾的占有;但她这种反抗,带着一丝的渴望。
原始冲动只需要原始的解决。几乎是一瞬间,垙的臀部急促的往前顶了一下,娴的身子随之一震,她推搡着他的手顿时软了下来。垙的来势是一种有力的、原始性的进入…长驱直入,他猛烈地占有她,好象一只野兽,他的来势象利刃式地刺进了她温柔的肉体里。娴觉着他的下体带着一种惊奇的力量与果断向她交触,但他那种强猛的,不容分说地的进入,是这样的奇异可怕,使她颤战。
顿时,一根又粗、又硬、又热的家伙满满当当的挤满了娴湿润的下身,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丈夫也曾带给她这种类似的感觉;陌生是因为这东西明显的与丈夫的不一样,它是那样的长而粗、那样的有力,刚开始她竟被它涨得十分的难受,尤其是当它被带动、开始前前后后的伸缩滑动的时候,她几乎要哭出声来。她在一种骤然的恐怖中紧绷而僵硬地抱着他。
就在垙进入她到底的那一瞬间,忽然他感到下面娴的那具躯体松弛了;不仅是松弛,而是绵软,那种交付于你、任由你摆布的绵软,仿佛被席醉、被枪击中。那正是女性肉体被征服的典型状态,不是被男性武力,而是被男性肉体。她的降服祈求着他男性的怜爱!
垙开始迅速而坚定地推动,一手握住她裸体的肩膀,一手按在她乳房上,注视着她的脸。他拉她,将她定住,继续为所欲为。他越发亢奋,就大力的运动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半躺着,靠住汽车的背靠,看着他在她上面的强烈动作,感觉着他反复深深地驱入她赤裸的肉体,直感觉到他射精时的骤然战栗,然后他的冲压的动作缓慢了下来。
但是娴仍然静静地躺着,也不退缩,眼泪慢慢地在她的眼里满溢了出来。
垙一动不动地感到了满足,他仍紧紧地搂着她,他的两腿压在她的两条赤裸的腿上,身子压在她的上面,用一种紧密的无疑的热力温暖着她。
停歇一阵,垙一点点地观赏著娴赤裸著的肉体,丰满的乳房,傲然的乳峰,在他蓄满了精气的身躯里,又激起一阵按奈不住的亢奋强劲的欲念,低下地道,”难为你了,我要再做一次”
娴软下来了的身子仍无劲,”…时间太长了…怕…”
垙似乎没有听到,他蹿起来,一把将娴拽住,很快地把他那坚挺的下体又深深地插入了娴,继续强劲有力的抽送著, …他这种男性的粗鲁和疯狂激起了娴一阵阵按奈不住的情欲。这时,娴感到下体挛缩,性快感辐射于全身,真正的性高潮形成一组波浪式运动。它有节奏地时隐时现,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地达到阵发状态,模糊,下降,却不完全止息,没有明确的界线,这种无限的感受延伸著。当高潮简简单单到来时,她意识不到快感是哪里来的;而她清楚地知道它来自阴蒂而非阴道。
垙最后一道潮水终于倾泻出来了。在他失控的那一刹那,娴吃惊地愣了一下,流露出一丝意外的惊恐,随即便忘情地畅游于纵欢的深情之中。他高潮射精后,仍停留在娴体内,和风细雨的在她的体内移动着…两手并不断摸捏着她的乳房…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多少回合,垙和娴彻底地完成了他们自己。这时,娴举过手腕,瞧着手表,开会时间已过十五分,她低声说:”开会了!开会时间过了!”
两人赶忙穿好衣服。
垙说:”开会小组发言,我还是第一个哩。”
“谁能想到一会儿你在将在会上庄重发言,这会儿却在干这事!”娴戏言。
他咬了她一口,说:”怪话!走啦,走啦。哎,你过会没人再出去。”说著就带着下身的淋漓,故作镇静地走出了汽车门,大步地走了。娴梳头描眉,重涂了口红,又整理了下衣服,直到看见外面无人时,才树叶一般地飘出车门,赶上垙,一同快步走向会场。
在娴近年来的记忆中,丈夫的冷漠,使她难以面对以往自己的性要求。虽然她不拒绝他性要求,在那种心情下和丈夫性交,她麻木地躺在他身下尽妻子的义务,只感到他的重量象一片黑云漂压在她的天空里。
丈夫动起情欲来是很磨人的,娴不知道他是否得到满足,反正他老是翻来覆去、折腾好半天,而她得到的往往是身体的机械性震惊和疲劳,而不是心理上的满足。往往是她被打垮了,精疲力竭了,但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泄。
有时,当他粗暴地做他的动作时,娴想像的是一个强壮男人在强奸她,这种想法便能使她达到一点肉体的性高潮。在想像自已被强奸时,和她性交的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他者。她自己都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得这么没出息,似乎有一点淫荡。她不由得鄙视起自己来,又有点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