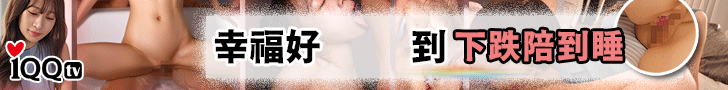有段时间,她一直遏制着自己的欲望,与丈夫错开上床的时间,即使是刚刚洗完澡,也将内衣内裤穿得整齐,而是在淡淡的愧疚中,享受着丈夫的乞求和对丈夫的拒绝所带来的虚荣感。这种心理从无意渐渐发展到有意,连她自己也出乎意料,她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在捉弄自己。
从垙进入她的生活那天后,原来与丈夫那时有时无的平淡性生活,突然变得激情飞扬起来。原来仅不时出现的性高潮,却能很容易就达到了。尽义务、献身、例行公事的感觉都淡化了,都没有了,彻底放松了,负担没有了,只想充分地体验和享受。这将错就错的错中错,反让她升华了性爱,常达到了”极至”的境界。她想,旦愿丈夫也体会到了那惟妙惟肖的变化,尽管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其它的交流,而这原始的接触, 也变得愈来愈少。
其实,从内心里,娴盼望着灵和肉的完美结合,盼望着生命中知音的出现。娴也知道,自己对这种完美的幻想根本就是一种奢望,美好的事物大都存在在梦幻里,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像自己这种被各种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享受一番荡气回肠的情趣已经很难得了!
怪不得有人这么说:”要找个爱你的人来做丈夫,找个你爱的人来做情人”如果能统一起来该多好啊!虽然她和垙之间,性是主要的。
那以后,垙一直是娴生活中的性伙伴,他们不像常人那么虚伪,他们之间是男女间的实质关系,那才是最本质的东西。他满足她正常生理需求,娴并想以此填充她的空白的感情空间。
垙的性欲一向也很强烈。他常会抑制不住的身上的欲火,强烈地要求见到她,她只要有空,都不会拒绝。然后他们就开始疯狂地做爱。在公众场合垙象个绅士,但在私底下,他会将她压在床上,对她做出许多”肮脏”却又解渴的事来。她也不再象第一次那么紧张、拘束了,变得很顺从,迎合著他的各种要求,常做得很棒,自己也得到一点满足。
刚开始,他们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十天半月地苟且一次;后来,他们便频繁的来往;有段时间,他们很狂热,次数频繁,有时一天多次。
他们一直保持着的伙伴关系。
第3章
娴和垙第一次一起出门活动是她丈夫搬离家后。
他们一同参加她一个同学的二婚婚礼。女方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结的婚,因为她本来就瘦,加上特意把礼服做宽了些,所以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知道以外,外人谁也看不出来。新娘穿着大红套裙,领子挖得很深,露出深层的乳沟,在大酒店门口风情地迎宾,娴笑嘻嘻地走到新娘面前恭喜,她把手放在新娘的腹部,悄声说:”你总算修成正果了啊。”新娘看了一眼四周,笑着将她的手打开说:”下一个就看你们的新纪录了。”
而娴抿著嘴,脸有点热地笑,她看了垙一眼,转向新娘说:”别指望啦,我都老徐娘啦;还是管你自己生孩子做黄脸婆吧。”
从婚宴上走出来,他们沿着江边一路走着。江风吹得很舒服,人不少,大部分是成双成对的恋人。
垙的臂挽著娴肩,慢慢地走在江风中。娴的神思扯了很远,忽然说:”新娘今天那套迎宾的礼服太大了点,她本来想遮住肚子的,没想到一做做那么大,晃晃荡荡的,看来这结婚礼服真的很关键”说到这里,娴的兴致忽然提了起来:”记得以前的结婚礼服是自己设计著的,现在想起来是太保守了一点。”
垙一声不响,没有接娴的话,也没转过头来看娴,他一直看着前方,步子频率有点加快。娴也只得赶紧加快脚步跟上他。
垙突然说:”你想过再结婚吗?”
娴愣了一下,想了想,回答说:”想过。”
垙:”那谈谈结婚这个问题好吗?我指的不是什么时候结婚,而是结婚的可能性。你真的认为你和我会有结婚的可能吗?”
经历了那么多感情风险,娴叹息地说:”现在谈结婚似乎早了点吧。等关系清了、我们成熟了,自然会考虑的呀。”如果垙不问,娴可以下意识地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它现在已经被垙翻了上来,使她不得不去面对它。
她又接着补充了一句:”别忘了,现你、我都是站在围墙内呐,我到算是要出来了的人, 你呢?”
可是,垙不客气地说:”别自欺欺人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至少可能性不大,对吧?”
娴闷声不响,她想驳垙,但是却再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觉得江风吹得有些凉了。她把手缩回来抱在胸前,说:”没有婚姻也可以过生活啊。”
其实,即使垙不说,娴也想找个适当的时候刺探一下他的想法的,她倒并不想要和他说什么时候结婚,而是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答案,这样她的心就会安定下来。
就在和垙沿江走回去的晚上,娴并没有告诉垙她怀孕了。在她和丈夫公式化的性生活基本没有了以后,她中断了避孕。
娴在酝酿情绪,在脑子里想像著垙和她谈那个问题,还有他和她在某一次共同创造的一个还不知性别的小生命。她没法开口,设想了很多个引子、很多个开头,想像垙会怎样回答,自己又怎么说。她在脑子里一问一答地演绎了整个过程,想从容不迫、有条有理。
进屋时,他的手机响了。
垙一面开门进来一面拿手机在打电话,不知是打给谁的,但从他的声音和表情上看,他很兴奋,一定是遇到高兴的事情了。
他进了门以后,顺手把拿着的包一把扔向沙发,然后也不坐下,就在客厅里迈开了步。娴躺在床上,看着他的身子过一会儿出现在卧室门口,然后消失,过一会儿再回来。他没有抬起眼睛看床上的娴,也没对她说一句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和电话里的人热烈地说著。
从他的话中娴知道他那个策划了差不多一年的生意终于获得了希望。这是一年来最影响他心情变化的事,对于他来说,周围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其它感觉顿时都不存在了,此时,他不会顾及到身边任何人的反应和感受,因为对他来说,那时身边是没有人的,或者都是无关紧要的人。现在,躺在床上的娴就是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娴早就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她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她决定不告诉垙她怀孕了,她没有信心。
垙的电话终于完了,他咧著嘴笑着,骂了一句话,然后一扬手把手机掷到沙发上,大步向卧室走去。娴在他出现在卧室门口的时候脸上浮起了软软的笑容。她躺着不动,她已经习惯了等待垙的反应。
垙脱下衣服和鞋子就上了床,把娴爽洁清香娇小的身体一把搂进了他怀里,紧紧地按在胸前,一句话也不说,娴也只是温顺地贴着她,一动不动。垙身上那男人的汗味和欲望笼照住了她,她闭起眼睛深深地吸进这股气味,让它们进入自己的身体,到达腹部,和那里的一团血肉会合。
垙的胸口起伏得越来越厉害,娴感觉到一股火正在他身体里越烧越旺。她睁开眼睛,垙的脸上正浮出混合著笑容的情欲高涨的表情。他的手伸进娴的上衣里,搓揉着她柔软的乳房,再顺着她纤弱的身体线条滑过细腻光滑的皮肤到达下面。娴悠长地嗯了一声,不由地半闭上了眼睛,全身被一种温水荡漾的感觉包围着。
他脱下她剩余的衣服、奶罩,两手抚摸着她丰腴赤裸的肉体,她丰满的乳房,又开始抚摸她的阴部,那里已经非常湿润了。当感觉到垙伏在她身上正要进入她体内的时候,娴想起了什么,一只手按著腹部,一只手下意识地阻止垙的进入。但是,垙咕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将她的手挪开,一挺身就进去了。娴在一阵直冲脑门的刺激感中长长地呼气长长地吸气,那种飞翔般的眩晕感在体内盘旋酝酿着。
现在,娴的身体里不仅有他,还有他和她在某一次共同创造的”他/她”他们的孩子,一个小生命。今晚,他/她的命运要被娴决定了。
娴知道她开始已获得性兴奋,性唤起已出现。她告别了她的灵魂,不再顾虑地只用肉体去做那很简单的事。可是,她做得很压抑…当他强劲有力的抽送时,娴强忍着不呻吟,默不作声地被动地接受他的”冲击”;她指甲都掐进了他的手臂里。她动人的脸开始亢奋,肌肉紧张,她将全身的力量全部集中到两腿根之间,但她仍无法最后完成。
垙在一大阵疯狂地骚动后,大声呻吟,他的极度性交欢乐随着一次突发的周身痉挛的射精动作,嘎然而止;一切都安静下来,夜风没有吹进房里来,空气慢慢地地附在他们已平静下来的皮肤上。
娴在垙身下,把脸抬起来,看着垙神清气爽、心满意足的脸,问:”今天怎么那么高兴?”
垙咧开嘴嘿嘿一笑,说:”这帮家伙,费了我一年的心血,终于搞定了。这事说了一天啦,烦了,说点别的吧。”
娴心里咯噔一下,心跳顿时加速起来。
停歇一阵,娴说:”今天的婚礼呀,折腾了那么久,她终于使那个老家伙娶了她,真是够有能耐的了。你知道吗?她告诉那个男的说她怀孕了,而且想要那个孩子,一定要生下来,她自己养,不用他负责,那个男的就跟她结了婚。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呢,结婚礼服差点都遮不住。她从小就特别有心眼儿,没想到结婚也这样。”
这就是娴在上床之前反反复复想的开头之一,她小心翼翼地把话题伸展开来递给垙,等待着垙的回答。
垙在听了娴的话以后,哼了一声,说道:”这种女人其实最让男人厌恶和害怕,用孩子来做人质拘捕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即使不得不屈服,但是他心里肯定恨这个女人,男人是最不能被强迫的,只有最笨的女人才以为那样是胜利了。你看着吧,你那个同学以后的日子绝对好过不了。”
娴几乎是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听垙说了这段话,她的脑子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反应过来,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放在了自己的腹部。她悄悄地闭上眼睛,把自己狂跳的心压回胸腔,然后深深吸了口气调整呼吸,接着说:”她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爱那个男人,想和他结婚,想为他生孩子啊。”
垙说:”爱是一厢情愿地决定,不顾对方的感受,只希望对方满足自己的愿望吗?这是自私、是控制。”
娴喃喃地说:”想和他结婚是控制他吗?”
垙说:”她也许并没有完全这样想,但最终结果就是控制那个男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婚姻本身就是控制男女双方的手段,使你陷入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因为你不是和一个人结婚,而是和社会结婚,太可怕了。”然后他一翻身起来说:”哎,一身都是汗,洗澡去。”接着,他在床上站起来,大步跨下床,吹着口哨向浴室走去。
娴的心已经掉在床底了,但手仍然放在腹部,呆呆地听着,垙的话一下子涌进她的大脑,虽然还没来得及被完全消化,但是明显的意思她是明白的。这个结论在她的脑子里像一盏雪亮的灯照着。
娴躺在床上,枕着凌乱的床单,看着他赤裸的身体走出自己的视线;她的手还放在腹部上,怔怔地摸著被他激烈冲创得发疼的骨盆和下身。接着,传来哗哗的水声,娴哭了。
此刻,她觉得有种很悲哀的感觉,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自大,但不让人讨厌的男人;后来成了一个霸气又强势的男人;在刚才,他又表现出冷酷而可怕的样子;不时,他却象个陌生人似的可以和你生疏的聊天,不着边际,却又透露出一些接近事实的事情…而在床上,他却又是一个掠夺而又贪婪的人,时常让人误以为他有多么乎你渴望你;但,一觉醒来后,你才会发现那不过是一场大川梦了无痕。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性的魔法所创造出来的。
娴又想,他渴望着自己的肉体,但自己却又能在他们的身体结合中察觉出他的疏离与刻意保持的淡漠,让她每每在事后都觉得更加的空虚、痛苦,到底什么时候,她才能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呢?
他究竟抱持着什么样的观感和情感?
每次想到这里,她总是不敢再往下想,因为越想,她就越无法面对自己这种肉体行为,可是每当想到自己身体主动投入,她又不禁迷惑。否则,为什么在他们的欢爱中,她能感到愉快呢?她真的茫然!
娴对腹中这个生命体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时候做出的。
去医院做流产是那天上午十点,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娴无人相伴,她感觉到医院白色的墙壁和那些穿着白色衣帽的人是那么令她颤栗,她独自行走在一片无人的但是却暗藏阴谋的空间里,各种各样的念头化身为翅膀的影子在白色的墙上扇动着,象死者的灵魂行走在那上面。
娴心里仍然感觉虚弱得要命,在妇产科那个淡黄色的门关起来之前,她只是笼统地茫然地害怕著,那种把她的肉体和心灵割裂开一个口子的痛还没有接触到她的身体,可这一切,在走廊尽头那扇门关起来以后,就要开始了。
所有的手续都是用一个假名办的。在等待叫号的时候,她震了一下,眼睛瞪大起来。恐惧的表情在她眼里颤动,她不由自主地向已经开启的黄色门走去。当门关上时,她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从打开的门里走出来时,她脸色苍白,没有休息,自个儿向过道外面走去。她终于跌坐在走道边的长椅上,脸色更苍白,眼神有点直,说:”我的孩子没有了。”
第4章
丈夫搬走后,房子里留下了娴一人,家俱是她买的,装修布置是按她的意思完成的,娴拥有这里的一切,但她心里空空如也。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没有找到真正爱自己的男人。
十多年的夫妻生活说完就完了,失败的婚姻给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最重的是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修复。一想起来,娴还是想骂人、想打架、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这种死一般的宁静太可怕了。
这种沉重打击使娴更加怀念自己的往事,回忆添补了那块荒了好长时间的感情自留地,对异性的好奇和向往,爱的萌芽和对爱的幻想。
女人总是要嫁的,这就是生活。娴带着对爱的幻想,嫁了,嫁给她那位后来分居的丈夫,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她看他的本份、样子可靠,她是这样想的。
这样,娴成了女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围绕着丈夫忙忙碌碌,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简单而实在,简单得就像是梦游一样。
接下来她有了孩子,当娴第一次见着自己的孩子,欣喜而来的泪水挂在脸上,亲吻著孩子粉红的小脸蛋,亲吻著孩子的微小的手指,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亲过来,是那么的依依不舍。孩子就是她,和她一样生下来就有着粉红色的健康的皮肤,不哭不闹,却动弹个不停,象条小泥鳅。她解开怀,当着众人的面给孩子喂奶。她奶水不够,孩子只能同时接受母乳和牛奶。她将鲜牛奶装在奶瓶里,怀里抱着孩子。
以后孩子就成了娴一生的希望。孩子整日吃得饱饱的,小肚子象个小西瓜似的。夏日里总爱撩起小褂,有节奏地敲著进行曲,拍著肚子到处走动。见了人就瞪直了圆圆的黑亮的眼睛,”啪、啪”地拍几下肚子跑开去,羊角辫在脑后一跳一跳地,蝴蝶结也跟着在飞。望着孩子长个儿,自己所有的郁愁的情绪都如阳光般的明亮起来了。
这就成了娴存在的证明,她才知道自己还活着,但感情生活象一汪长满青苔的死水。
她的确没有认真想过,十多年就像是一场梦,懵懵之中就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