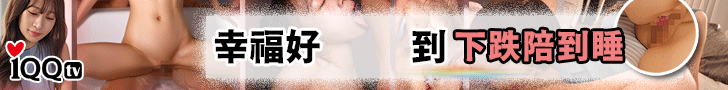初到霓虹燈下的都市,他覺得五彩繽紛、光彩奪目,不過他似乎入世未深,並不知道在這個物質更加豐盛的「森林」裡同時也是弱肉強食、危機四伏。享受慣淳樸的鄉村生活的偉強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找工作的時候老是遇上老闆請他吃的閉門羹,還試過被別人搶錢包。禍不單行之下,他沒有放棄,反而積極面對,因為他知道,在這個大城市中總有一處地方有白雪的蹤影。
每天,偉強為了工作,從不知何人的小攤裡販賣假貨。為了躲避海關追捕,經常在大街小巷中來回穿梭,過著朝不保夕、「亡命天涯」的生活。與此同時,他也四週打探白雪的消息。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消息打探不了,自己不但消瘦了不少,還露出一副頹廢的模樣,其實比起乞丐好不了多少。
只住在簡陋板間房的他為了不讓鄉下的雙親擔心,沒有把自己非人的生活如實告知,反而在信中寫下自己如何出門遇貴人,如何打理小店之類的話。
時光飛逝,已經步入了離鄉別井的日子的第二個年頭。北城的冬天一樣會下雪,只是比起鄉下,不但少了一種溫柔的感覺,而且多了幾分憂鬱的寂寞。這個屋子不但小,而且幾乎密不透風,唯一的一個窗戶就只有數平方尺。他總是看著窗外的世界,即使狹小,可是總算看到雪景。只有它是偉強在屋子裡和外界聯繫的唯一橋樑,只有它令偉強在北城裡得到的唯一安慰,尤其是當自己看到外面雪花飄飄的同時,他思念在故鄉中的父母、鄉里,更加思念多年不見的白雪。
「白雪,你到底在哪兒?」這句話幾乎成為了偉強來到這裡才說的口頭禪。吃飯、睡覺,甚至是做夢都會說著。沒有看見白雪的話,他一定不會就此死心。
又過了兩三年後,今年的冬至來得特別早,城市裡已經有很多人穿上羽絨。身上連毛衣都沒有的偉強,冒著嚴寒在街道的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蹲下,鋪上報紙,放下冒牌手袋和皮包,等待著路人的「施捨」。
一直等到傍晚,他連五個手袋都賣不出去。晚上七點整,太陽公公早已跑回自己的窩裡過冬,月亮姐姐則懶洋洋地爬起床來,無奈地繼續肩負起指引迷途羔羊的使命。整個天空變得一片昏暗,冷風吹過樹梢發出如鬼哭神嚎的叫聲,令人膽顫心驚。街上沒有行人,因此有些路燈開始鬧情緒不願意工作,這條在早上熱熱鬧鬧的陽關道頓時變成了現在偉強一人的私家路。
他迷惘地在黑夜中尋找光明。沒有了白雪,對他來說仿如沒有了希望。他含辛茹苦熬到今時今日,僅僅為了見上白雪一面。自己沒有考慮清楚,她可能已經遠走他方,也許在某個地方過上安樂的日子了。現在想也沒用,偉強現在就只有填飽自己的肚子。
突然,飢寒交迫的他看見前面有一家食店亮著燈光,而且從遠方不時傳來白米的芳香,就好像見到了一線曙光,用盡吃奶的力氣跑過去。到了食店的門口,發現可謂座無虛席,桌上的海鮮、湯羹更加應有盡有。他已經等不及了,走進食店向裡面的店員購買食物,可是他身上根本就帶不夠錢,被店員白了一眼後,只能要了一個炒飯打包。
食店裡的眾人吃得津津有味之餘,還經常傳出歡樂的笑聲。而孤單的偉強憶起那時自己的家人和白雪的父母一起吃飯,觸景傷情下,眼角在電燈的照射下露出一絲淚光。他為了不讓別人看見,很快就走進漆黑的環境中。
他在街上隨便地找了一算是比較明亮的地方坐下,打開剛才在食店購買的東西,冷冰冰的飯盒裡面其實有點餿味,要是仔細一看,還發現蔬菜都已經有點發黃發霉,似乎是幾天前的殘羹冷炙,別無選擇之下他顧不上歧視,只好吃下去。
偉強越吃越不是滋味,忍受著那愈發濃郁的餿味,已經把飯盒完成了三分之二。淚水從他的眼眶中一滴一滴地往下墜,為這盒「豐富的盛宴」增添「美味的湯水」。完成了在冬至的晚餐,他拿出懷中的口琴,在無人的大道上吹奏出那些耳熟能詳的音符。寂寞的童謠迴響在附近幾所建築物之間,聲調是一樣,可是感情就大相徑庭。他漠然地看著前方,不知過了多久,才累得放下口琴。
忽然,從他的身後響起汽車的剎車聲。他轉頭望過去,看見下車的是一男一女,兩人雙手十指緊扣。即使夜晚的能見度並不高,藉著燈光也可以大致看清楚他們的相貌:男的不比自己高,身穿厚重的大毛衣,樣子有點猥瑣的瘦削男人大概四十齣頭。當偉強再次轉過頭去看女子時,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雖然這名女子全身都被衣服包裹,但是臉上那個清秀的模樣,還有那顆與十年前仍然不變的小黑痣,他情不自禁之下叫了一聲:「白雪!」那對男女同時看向偉強,尤其是那名女子,反應很大。儘管沒有實質的證據,但是其一顰一笑,甚至氣質,都讓偉強估計她七八分就是自己多年要找的人。他迫不及待再次把手中的口琴塞到口邊,熟練地吹出那首童謠。
「是……是他……」儘管聲音不是很大,可旁邊的男人還是聽得一清二楚。
「你認識他麼?」那名長相猥瑣的男子詢問懷疑是白雪的女子。
「不,不是。或許我認錯人了,他不可能在這裡的。我……我不認識他。」女子猶豫了一下,接著道。
「但是他知道你的名字啊?」男子貌似很好奇兩人的關係,繼續追問道。
「或許……或許是從別的地方知道了我的名字吧!看他髒兮兮的樣子,肯定不會是我認識的人。來,不用管他了,我們……我們上去舒服一下,好麼?」女子向旁邊醜陋的男人拋媚眼,牽著他的手,頭也不回的向屋子裡進去。反而那個男人對偉強有幾分興趣,在走進屋子之前還扭過頭來看了他幾眼。
偉強正想追上去,門已經從裡面鎖起來了,無論他在門外如何叫喊,如何敲打,裡面都沒有絲毫動靜。
十分鐘……二十分鐘……轉眼已是幾個小時後的夜深。路燈開始熄滅,他雙手抱著發冷的身體坐在門前,傻乎乎地一直在不停思索:為什麼她會變成這樣?想了老半天,他終於想通了:大概已經是十多年沒見了,她忘記了自己其實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想著想著,他決定明天再來這裡。
躺在自己的狗窩裡,他徹夜難眠,不是因為傷心,而是因為興奮。
『幾年的光陰總算沒有白費,雖然她沒有認出自己,若是真的到了重逢的一刻,我到時候再為她吹出那首曲子,她一定開懷大笑的……』偉強一邊在心裡打著這個如意算盤,一邊就在傻笑中渡過了這一個難忘的晚上。
晨曦之光,透過窗戶直射在偉強的眼皮上,自己調教的鬧鐘接著開始運作,馬上響遍整個房間。起床後的他依稀記得自己昨天晚上因為興奮而失眠。他隨便梳洗了一下,吃了些麵包,馬不停蹄趕往那個公寓的前面。
清晨的陽光本來就不太強烈,加上薄霧瀰漫,他身體難受之餘,因為視野的關係而找不出公寓的確切方位,心裡也是五味雜陳。找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偉強才終於找到女子的住處。此刻,太陽已經開始照耀在頭頂,薄霧也開始消散。現在才看清楚其真實外貌——三層高的洋式公寓與嶄新的外牆一下子映入眼簾,貌似剛建造不久。門前站著兩個高大的人,當偉強靠近的同時,被他們拒於門外。
「求你們行行方便好麼?我想到裡面找一個女人……」
「這裡沒有你要找的人,給我走開!」其中一個魁梧男兇神惡煞,擺著手勢示意偉強離開。當然,偉強並沒有離去之意,反而想往裡面探頭看個究竟。
「喂,你是來搗亂是吧?再不走的話,我們可要動粗了。」
「求求你們了,我只是想找個人,不是來搗亂的。」二人見偉強不肯離去,於是把他給抓起來。
「等等,你們都做什麼了?」突然,從外面走出來兩個人,是昨晚那個猥瑣男和疑似白雪的女子。
「大哥,是這個混蛋一直在這裡搗亂,不給他一點教訓是不行的。」魁梧男展示著自己的肌肉道。
「這個男的……對了,寶貝,昨天他不是叫了你的名字麼?弄得我昨天晚上和你都做不好那事,他是不是你以前的舊相好啊?」
「怎……怎麼會呢!我壓根兒就不認識這個人。」那名女子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你是白雪麼?你真的是萬白雪麼?我是偉強啊,鄔偉強啊!跟你在村子一起長大的男孩呢,你全部不記得了麼?」
「我根本不認識你,少來這裡攀關係了。」女子厲聲的斥責比起魁梧男的辱罵來得更加奏效,猶如當年白雪告訴自己要分開之時一樣,一把剪刀對著心臟猛刺進來。偉強絕望地低下了頭,在心裡痛罵自己:要不是認錯了人就是真的被人遺棄了。而正在這時……
「是麼?把他抓過來!」
猥瑣男抓起偉強的頭,偉強的眼神空洞無物,彷彿心裡已經默認自己面臨世界末日一樣。
「你到底有沒有什麼工作啊?」
「什……什麼?」他意料不到猥瑣男會如此問他。
「我……我有……」
「什麼工作?」
「賣假貨的手袋……」
「哈哈,假貨手袋……看來你的情況並不樂觀呢!」
「那就好。」他轉過頭去,對著女子繼續說道:「之前不是走了一個打雜的工人麼?不如就讓他來我們這裡幫忙好不?」
「這……」女子欲言又止,接著有點不情願地就點了點頭。
「這樣吧,明天你來我們這裡,就幹打雜、清潔什麼吧!我雖然不知道販賣盜版能賺上多少錢。好不好?」
「什麼?我做,我真的做。」偉強沒想到對方居然會說著這樣的話,於是斬釘截鐵地答道。
在這裡的所有人,包括白雪,都不知道猥瑣男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單純的偉強心想這樣既然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又可以更加親近眼前的她,就笑著答應下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後到底將會面臨什麼問題……
搬過去的偉強,正如猥瑣男所說,真的做起打雜的工夫。他多次向白雪探聽身份,但是白雪似乎有點厭惡其煩,到後來根本就不向他搭理。
一個晚上,雷電與雪雨交織在一起,狂風不斷使一棵棵大樹搖擺不定。然而除了偶然的雷聲之外,關上大門、窗戶後的室內只可以清晰聽見秒針的擺動。這個時候偉強看著窗外白雪茫茫,不由得回憶起孩提時代和青梅竹馬的玩伴嬉戲、看雪景的情形。本應該上床睡覺的他,卻聽到了除此之外的第三種響聲——女人的呻吟聲。這是他進入這個大宅以來,首次聽到最詭異的響聲。他不知道這些響聲為何會出現,他只知道發出這些響聲的就是自己一直要找的白雪。
他站起來,一直追尋著聲響的來源,終於到了二樓的主人房門前。房間的門沒有關好,漏出一條發出光芒的門縫,當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窺看裡面的時候,發現此刻正好上映一場不能錯過、精彩絕倫的大戲:露出全身肌肉的猥瑣男把一絲不掛的白雪壓在身下,那條同樣充滿「肌肉」的肉棒子也在那個洞口不停進出,每挺進一下,猥瑣男的屁股就會抖動一次,白雪那銷魂的叫聲也會迴響在四壁之中。
偉強在農村時,無可否認閱讀過不少損友送給自己的色慾書籍,可是從來沒有真正觀看過真實上演的情景,身體情不自禁地興奮起來,尤其是他那條沒有甦醒的小弟弟,終於也要抬頭見人了。
「啊……啊啊……大力一點……好棒……」他沒有看見白雪的表情,但是從語氣和聲調來說,的確很享受這種動物與生俱來的活動。
「叫大聲一點,寶貝,我要你大聲點……」猥瑣男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難聽,還是一如既往的低沉。不過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對比懸殊的男女,尤其是當癩蛤蟆在吃天鵝肉之時,在「吃」的人才顯得痛快,在看的人才感覺虐心。
那個偉強自嘆不如的強壯軀幹,正在蹂躪自己的「妹妹」,糟蹋自己朝思暮想的人的嬌軀。這種思想令他自卑之餘,還帶有絲絲的刺激。
突然,他的面前出現了兩個虛幻的「自己」——一個身穿白色衣服,一個穿著黑色衣服。白色衣服的遊說自己,不要再繼續看下去了,趕快阻止這場不倫之戀,這樣只會令自己好過一些。而黑色衣服的則勸諭自己繼續欣賞這場「生死格鬥」。對於兩個決定的抉擇,偉強都覺得十分困難。
他深知這個並非不倫之戀,反而是你情我願,而且這種情況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觀看得到,偉強為了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無形中使他的慾望戰勝了理智。
房內的「打鬥」愈發激烈,撞擊聲和呻吟聲已經不僅支配了運動的二人,還刺激著房外的偷窺者。而這個「門外漢」似乎從數秒前就已經被房中兩人出色的演繹而吸引,視線變得無法自拔,身體更深陷其中。
「唔……嗯嗯……用力點……」
「寶貝,我來了!」猥瑣男彎下自己的熊腰,親吻著白雪的櫻桃小嘴,品嚐著口中新鮮的蜜汁。那條強壯的管道暫時在洞中停留,鼓脹的陰囊中蘊含大量豐富的精華,等待灌溉貧瘠的「肉地」。
不管外面多麼冷酷,裡面的男女交合儀式可是進行得如火如荼。很快,猥瑣男的寬背在「溫暖」的房間中開始冒出微微的「白煙」。不停轉換姿勢的白雪不比猥瑣男舒服,不過在體力接近耗盡的同時,正在盡最後的努力衝刺,正在嘗試享受性愛的最後一刻。
當猥瑣男抬起他的身子時,還可以看見白雪那雙養得肥肥大大的小肉兔呼之欲出,要是能夠在上面拿捏一番的話,必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猥瑣男看準時機,粗大醜陋的雙手在上面亂抓,人如其名的兩隻小白兔就這樣被粗魯地捏出痕跡。
另一方面,偉強掏出自己的陽具,效仿面前的猥瑣男。沒有確實的目標,沒有溫暖的觸感,有的只是微開的門縫,他就這樣利用房門給自己帶來了來到這個異地的第一次高潮。
當自己完事後,裡面的情況仍在不停地繼續。猥瑣男的臀部上下起伏著,貌似是在欺負白雪那神秘的敏感地帶;下面的兩片小唇合不攏嘴,正在吞吃充滿活力的「棒棒糖」,而那飢餓的「腹腔」更是被填得肚滿腸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