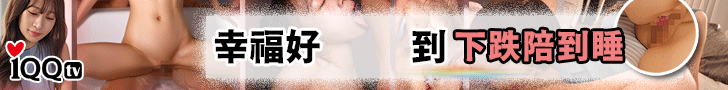看著那猥瑣男滿足的表情,偉強不知不覺生起妒忌之心。他用自己瘦削的身體和猥瑣男那強壯的身姿對比,特別是下面的那個生育工具,簡直就是魚卵和鴕鳥蛋的區別,難怪白雪在他的面前無法擺出拒絕的姿態。
「射……射了……」猥瑣男立即雙腿併攏,全神貫注地把身體盡量壓低,胯下兩個肉囊開始運作,彷如一個水泵一樣,把裡面的肥料往白雪體內灌注。大汗淋漓的猥瑣男抓住最後的機會全力衝刺,用手按摩自己的陰囊,希望在僅有的時間排出更多的量。也由於激烈的運動,肥料的保溫工作做得很完美,何況在外面還下著大雪,在這種對比明顯的環境底下,被澆在花心上的白雪正感受體內熱力的澎湃,就像一個歌女在詠唱到高潮時似的,發出醉人的歌聲。
冷靜下來後,他發現白雪已經不再是他以前認識的那個清純女孩了,現在的她,只是一個只會享受性愛帶給自己快樂的墮落女子。但不論結果如何,他打從心底裡不覺得這個是一個變壞的蘋果,而是一隻正在蛻變的天鵝——自由自在地飛翔,無拘無束地去愛。
他來到城市後,改變了他的思想,認為年齡不再是問題,只要用心的話,就一定能夠開心快樂,希望白雪以後呆在猥瑣男的身邊會更加幸福。只要看到這樣的白雪,他都會覺得心滿意足。
既然如此,接下來的日子,他都不會放過欣賞的機會。每當春色無邊之夜,就是自我安慰之時。白雪對他依然不瞅不睬,他已經不再在乎這些無關痛癢的事情,要做的就是默默地守候在她的身邊。不管是她多麼無理的要求,他都堅持去完成。他還是和小時候一樣,對白雪關懷備至,然而,這個女人對於單純的他卻視若無睹。
一天,他拿出銀色的口琴,在客廳中吹起來。不到五分鐘,偉強聽見下樓梯的腳步聲,原來是白雪。
「吵吵吵,就只會吵,你不知道好煩人麼?」得勢不饒人的傲慢態度沒有讓偉強覺得異常難受,畢竟已見慣不怪了。
「好的,我吹小聲一點可以麼?」
「不允許,我不要再看到這個破口琴出現在這裡!」白雪破口大罵,完全沒有要給偉強任何情面。
「不過這口琴是你送給我的,我不可能捨棄它,而且我們不是還有承諾麼?我和你見面之後,我會吹口琴……」還沒等話說完,她搶過他手中的口琴,從窗外扔到樓下的草叢中。
「啊!」撕裂的一聲慘叫,令偉強近乎崩潰。他馬上走出大街,尋找口琴的蹤影。而就在他的身後,大門被某人無情地關上,還伴隨著一句無情的話:「神經病!」
偉強找了很久,才找到滿身泥巴的它。無家可歸的他,在大街上流離浪蕩,像瘋子一樣。他還是沒有怪責過白雪,嚴格來說是沒有資格去怪責她。他單純知道她的轉變是自己直接或者間接造成。此後,他沒有再去找白雪,似乎是不希望
白雪見到自己之後會不高興。當然,猥瑣男對於一個陌生人來說,自然也會不聞不問。
一切回到起點,應該是說比起點更加殘忍,原來那個她是如此憎恨自己的。他返回以前那個狗窩,繼續去過那非人的生活。一個多月後,白雪紛飛,他拿出那個口琴,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的白雪都回想了一遍,能夠見到她,哪怕只有她的倩影都已經心滿意足。
他踏出房子,經過苦練,終於可以在大雪下不但吹出動人的樂章、更吹出了從懂事到現在的喜與悲,可惜那唯一的觀眾並沒有如他所願的坐在自己面前。不知道是天意弄人還是剛好巧合,就在不遠處居然傳來了久違又熟悉的聲音,隨後又是一下震耳的巴掌聲。
「白雪,對,是她!」偉強趕往聲音的源頭。真的看見了白雪,可是她正跌坐在地上。
「我告訴你,別再來煩我。」猥瑣男的聲音同時響起,看情形他剛好打了白雪一個耳光。
「求求你,就算你不顧及我,也要顧及肚子裡我和你的孩子,好麼?」猥瑣男以前每天晚上都必定餵飽白雪,這樣想的話,她懷孕是遲早的事。不過對於偉強來說,還是有些倍感唐突。
「少廢話,我玩過的女人何止你一個,要是每一個都來我這裡鬧的話,豈不是忙死我了麼?快給我滾,有多遠滾多遠,老子已經不再需要你了。滾!」
瀰漫著粗言穢語的大路讓偉強頓時感到非常噁心,他二話不說,上前就想給猥瑣男一拳。不過他根本不是猥瑣男的對手,而且猥瑣男旁邊還有兩個魁梧男。偉強沒有放棄抵抗,他為人善良,況且白雪遭遇這種對待,他無法擺出事不關己的姿態。身為「哥哥」的他,有責任要保護好「小妹」,所以他不管怎樣都向摸不著邊的猥瑣男發動無意義的攻擊。
偉強最終被打得滿身傷痕。猥瑣男走後,他撐著沉重的身體把白雪扶到自己的房子。以後,白雪都住在偉強的家裡。儘管偉強對白雪心存好意,由於沒有表白,一直真的對她如妹妹般相待。白雪每天都愁容滿面,望著在那唯一的窗戶發呆,即使偉強主動和她對話,她也不為所動。
隨著時間的推移,白雪偶然也會說一些話。到了後來,她把那件事淡忘了,已經到了臨盆在即……
白雪曾經想過不要孩子,是偉強努力地勸阻才放棄,他覺得孩子是無辜的,不應該扼殺一個小生命。最後,白雪才決定生下來。當然,在醫院出生的小孩很可愛,樣子像白雪一樣,偉強對其視如己出。他依然是白雪的「哥哥」,所以這個寶寶沒有爸爸,只有叔叔。
日子長了,兩個人都要為工作而奮鬥,於是他抱著孩子,第一次返回自己的老家,把寶寶託付給自己的父母後再回來——說這個小孩是自己所出的。偉強沒有想過和白雪結婚,因為他覺得這樣就已經足夠了,不需要哪些繁文縟節。
冬天的傾盆大雨可不是說笑,偉強看見白雪被淋個正著,心疼得難受。而她的身體也開始發冷,最後發高燒,偉強用厚重的被子蓋在她身上,看著她急促的呼吸,覺得不能再延誤病情。
就在偉強要離開之際,忽然她抓住他的手:「對不起……」白雪因為高燒而有點紅潤,看起來更加可愛,可惜眼角不斷滲出淚水,又使人頗感憐愛。她語氣之中沒有感到傲嬌,反而是愧疚。
「怎麼了?」
「對不起,對不起……」白雪更加激動,令偉強丈二和尚,不明所以。
「我知道你很辛苦,不過不要緊的,我就去給你買藥。」
「不要走,好不好……」白雪的眼皮快要睜不開了,可她還是不希望偉強離開。
「那好吧,我在這裡陪你。」偉強無奈之下,只好摟著這個「林黛玉」。等她睡好之後,就問鄰居借了自行車,離開了家,往藥店去買藥。
他沒有理會在空中落下的大雨,沒有理會在路面疾馳的汽車,也沒有理會在身旁不斷發出的雨聲,只是在柏油路上靜靜地運動。突然,就在他不察覺的情況下,右面逐漸逼近了一道強光……
*** *** *** *** *** ***
白雪一直對猥瑣男死心塌地,換來的居然是一個無情無義的巴掌;她平時對偉強頤指氣使,得到的反而是不離不棄的關懷。她心中的黑霧已經退卻,終於看清楚哪一個是負心人,哪一個是癡情漢。她不瞭解現在可以亡羊補牢還是為時已晚,但不管如何,她真的很希望能為偉強作出少許補償。
昏睡的白雪,在夢中看見了在小時候出生的村落與偉強一起玩耍的情景,還有那個孩提時代的承諾。接著,就是自己來到這個城市後遭遇到的一切:
白雪的父母來到這裡,雖說是工作,其實並不比農村要好。
首先遭遇到可恥的老闆:
不僅剋扣工資,還理所當然地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每天工作12小時,還不給假期,有時還要他打雜,簡直比死更難受。每天晚上,她看著爸爸那疲怠的臉龐,時而大喜,時而大悲,最後還由於這樣而神經失常,需要接受精神治療。媽媽更是啞巴吃黃連,既要照顧年幼的白雪,又要在外賺錢。當然,這個老闆是締造白雪家庭破碎的元兇。
接著輪到可怕的房東:
剛開始的時候,不斷增加租金,令父母苦不堪言。但是白雪一直都不喜歡這個房東,因為他總是色迷迷地看著白雪的母親。由於母親很年輕的時候就生下了白雪,以至於看起來依舊美麗動人,這個房東不過是一個胖大叔想吃天鵝肉的癩蛤蟆。在其身邊保護的老公因為老闆的關係變得痴癡獃獃,那麼房東就能趁虛而入,開始向母親獻殷勤。其實母親根本就不喜歡他,但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拒絕。
一天,房東自願走過來為白雪的家裡安裝電燈,母親不想他來,但無計可施下被迫接受了。他還黏在白雪的家裡,喝得酩酊大醉,後來趁著父親去接受治療不在家,他又有幾分醉意,就在父母的臥室裡把母親給強暴內射了。
白雪記得那天,她只可以躲在衣櫃裡一言不發,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禽獸一樣的肥大叔施暴,尤其是當他扯破母親的衣服,還把那條肥大的、不知道是何物的東西放進母親的體內。從那時起,她就對那樣的東西有了反感,看著自己母親被禽獸「播種」,那種經歷實在難以忘懷。
一個多月後,母親因為那次被施暴有了小孩,房東當然不會理會這些,一定要母親和父親離婚,又不允許她打掉孩子。母親就是溫柔又膽小的人,既沒有反抗房東的能力,又不忍心殺死肚子裡的孩子,自己原來的丈夫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康復。結果,她真的在威迫利誘之下簽署了離婚協議書,再被迫與胖大叔房東結婚。而那個時候,白雪就變得無家可歸,到處流浪。
最後是無情的司機:
就在白雪無依無靠之下,居然被那輛車撞到了,受了重傷。似乎是老天爺的作弄,讓她遇上猥瑣男相救。
不幸的事件令白雪整個人改變了很多,也不知道是否老天爺的戲弄,流浪街頭被猥瑣男所救,最後成為了他的女人、他的玩物。她以為一切都會好起來,直到遇見偉強。她不喜歡偉強,因為她不想自己的過去被猥瑣男知道。
一切一切都發生得太過突然,自己又懷了猥瑣男的骨肉。那個小孩明明和偉強沒有半點聯繫,居然得到了他的重視、他的照顧,反而猥瑣男就是一個典型的「陳世美」……
「白雪……白雪……」
白雪勉強抬起疲憊的眼皮,朦朦朧朧地看見偉強站在自己面前。奇怪的是,他的身上居然沒有一滴雨水,他的臉上也沒有一絲血色。
「你剛才一直都在我身邊麼?你沒事吧?看樣子你好像有點不太好呀!是不是出去買藥的時候著涼了?」
「……」偉強沒有說話,想了想,最後說道:「我沒事。等你睡著了之後我就出去買藥了。來,吃下去吧!」他打開那包藥片,倒了幾顆,讓白雪吞下。
「躺一下吧,這樣會舒服一點。」偉強溫柔的聲音傳到白雪的耳中,令白雪覺得原來真真正正得到男人的關懷,比起性愛的高潮來得更加實在。
「你可以再繼續這樣陪著我麼?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白雪偎依在偉強的肩膀上,正好和當年看流星的兩個小孩一樣在談心,只不過年齡、環境變得不一樣吧了。她把自己來到這個都市後的所有經歷都告訴了偉強,他也在全神貫注地傾聽。
「很久都沒有這樣了……」白雪並非病重,但言語之間還是力有不逮。偉強發揮出「哥哥」的本能,沒有埋怨半句,沒有悶哼一聲,只靜靜地守候在白雪的身邊。
風吹落葉,貌似在給兩人一些提示,他們彼此望出窗外,看見漫天風雪,覆蓋了這個對於他們來說很不幸的城市。這是自他們生活在這裡以來,看到最美麗的一次雪景。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的承諾呢?」
「是指……我們在這裡第一次見面,你就給我吹奏童謠的事兒麼?」
「嗯!」
「好……好想聽啊……」白雪拖著沉重的身子,再次偎依在偉強的懷裡。
偉強從懷中拿出口琴,吹奏起來。這首不是別的,正是童年的那首兒歌,它已經和正式的曲調沒有兩樣,剛好與眼前的雪景共鳴,彼此都享受整個過程。就在完成之時,白雪頓時感到意外地發睏……
「對不起,我是時候走了……」偉強突然站起來,雙手扶著白雪的肩膀,讓她好好地躺下。
「走?你要走去哪裡呢?」白雪無力支持發病的嬌軀,只能任由偉強擺佈,全身開始有點乏力,眼皮再也無法支撐。她眼前的偉強開始變得若隱若現,即使本能地伸出雙手也抓不住他的身體。
「再見了,白雪,我真的要走了,希望我們……」說這話時,白雪還可以聽見他的哀愁、他的懊悔。沒等到說罷,偉強已經消失了,而白雪的眼皮也只得緩緩放下……
清晨的早上,白雪被電話的鈴聲驚醒。一覺醒來,疲勞不但消逝,更精神奕奕、神采飛揚。她接過電話,對方是醫院打來的,要求她立刻前往。原來昨晚發生了一場非常嚴重的交通意外,一位騎自行車的男性被貨櫃車撞倒在地。
當白雪揭開白布,看到的是一副再熟悉不過的樣貌——和昨晚看見的偉強一樣,面目血色。她的眼淚煞時如泉水般湧出眼眶,一滴滴地落在偉強的臉龐上。聽醫生說,當路人發現他時已經遍體鱗傷,口中吐出許多鮮血,但是很奇怪,他的手裡牢牢地握緊一個口琴,還有一張彩票……
愛過、恨過、痛過的白雪,頓時在醫院裡暈倒。當偉強不在的時候,她才懂得珍惜。縱使他不在,還有那個口琴長伴自己。
不知道是上天憐憫,還是偉強的保佑,偉強生前留給白雪的另一樣遺物——彩票居然中獎了,是頭獎幾千多萬!但是,她並沒有改變眼下窮困的生活,而是用這些錢開始了自己放眼世界的征途,這是因為她知道自己還沒有履行和他的承諾——看遍整個世界。她代替偉強的雙腳,踏遍大江南北;她代替偉強的雙眼,看盡風土人情;她代替偉強的雙手,寫下沿路點滴。旅程之中她並不覺得孤單,因為那個口風琴就像偉強一樣,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邊。
二十年了,年輕貌美的女子,轉眼就是徐娘半老。在浩瀚的沙漠、無邊的海洋、廣闊的平原中,她都覺得不如自己出生的那條村子,畢竟那裡有她的兒子,也是她的根。
那天,她走進了二十多年來從沒有踏足的土地,正好和她離開時一樣,都是寒冬。她一直沒有去看自己的孩兒,只因之前沒有履行自己對偉強的諾言,而現在,她終於回來了,可以履行對兒子的承諾了,即使兒子不認得自己也無所謂,就像偉強一樣,默默地陪伴在自己身邊。
雖然花草依舊,卻物是人非。村中的變化猶如翻天覆地,不認得的路、不認識的人隨處可見。她想懷緬那個與偉強童年時代的基地也不翼而飛,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嶄新的橋樑。就在她走過橋樑時,大橋突然崩塌,白雪伴隨著積雪一起被壓在橋下。
白雪失去過雙親,然後因為自己的任性再一次失去了偉強,已經後悔莫及。她不希望再繼續失去這次難得的機會了,於是自己欣然接受了這個命運的安排。
偉強的死,的確給白雪很大的打擊。不過正因為如此,偉強的死,與他遺下的口琴,都成為了白雪的手電筒,在這二十年間,陪伴她經過浩瀚的沙漠、無邊的海洋、宏偉的山脈……正好一直指引了在黑暗中徘徊、迷惘的她一條帶有曙光的出路。她沒有抵抗,任由那些積雪壓在自己的身上,也許這樣的結果是命運、緣份,也是自己最希望要的吧!
當拯救隊救出白雪時,發現她已經停止了一切呼吸和心跳,其彎曲的身體貌似要保護什麼似的。尤其當伸展開她已經變得僵硬的身體,隊員們都紛紛感到十分不可思議:除了身體完全沒有皮外傷外,還有一處異常詭異的地方:平時救出的死者都是痛苦得面容扭曲,然而,她居然帶著幸福的笑容,而且她的雙手由始至終都把一個殘破不堪的口琴死死地按在自己的胸前。
村中已經沒有人知道這位「異地的旅行者」究竟經歷過什麼樣的遭遇,但是從她那安詳的容貌推斷,可算是對人世間沒有任何留戀了。和她的笑容一樣神秘的口琴,至今一直都是不解之謎。而這個秘密,隨著她消逝的靈魂,也一同長眠於出生地的漫天風雪之中……
*** *** *** *** *** ***
很多人都不懂得珍惜,不管是人是物,當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才懂得後悔。尤其是親人,「子欲養而親不在」很好地概括了由於某人的幼稚,使一位親人離世,即使到了現在仍一直刺痛其心。請各位看倌注意,珍惜眼前人,尤其是親人,可一不可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