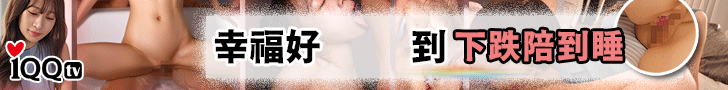一天,O的愛人帶她到他們從沒去過的那一區散步,像是蒙蘇里公園、蒙梭公園。在公園轉角的一個路口,那裡本來沒有計程車候客站,但這天他們在公園裡散了步、坐在草地邊上的時候,看見了一輛有計程表的車,很像是計程車。
「上車!」他說。她上了車。再不久就要天黑了。這時是秋天,她身上穿著跟平常一樣的服裝款式:高跟鞋,一件搭配百褶裙的套裝,一件絲質內衣,沒戴帽子,但戴著一直套到上衣袖口的長手套,並帶著一個皮製手提包,裡面有證件、粉盒和口紅。
計程車緩緩往前開動,和她同行的男子沒跟司機說任何話,但他拉上了左右兩邊車窗上的布簾,以及後面的布簾。她以為他要吻她,或是要她愛撫他,所以脫下手套。
但是他說:「妳身上的東西太累贅了。把手提包給我。」她把手提包給了他,他把它放在她拿不到的地方,並說:「妳也穿得太多了。解開妳的吊襪帶,把絲襪褪到膝上。」她覺得有點不安。
計程車開得更快了,她擔心司機轉過頭來看。終於,她把絲襪半脫下來,光裸的大腿在裙子下不受任何拘束,讓她覺得很不自在。解開的吊襪帶在她衣服裡面滑動。
「脫下吊襪帶。脫掉內褲。」他說。
這很容易。只要把手放到腰後,稍微抬高一下臀部就可以了。他從她手中接過吊襪帶和內褲,打開手提包,放入其中後再闔起來。然後他說:「別坐在套裝和裙子上。妳應該把它們撩起來,直接坐在座椅上。」座椅是仿皮漆布,又滑又冷,貼在皮膚上的感覺讓人忍不住一凜。
然後他對她說:「現在再戴上妳的手套。」計程車一直在行駛中,而她不敢問荷內為什麼動也不動、不再說話,也不敢問他這件事對他有什麼樣的意義:讓她這樣靜坐著不動,這麼衣不蔽體,卻這麼正經地戴著手套,坐在一輛不知道要開到哪裡去的黑色車子裡。
他沒有叫她做什麼,也沒有不准她做什麼,但是她不敢交叉兩腿,也不敢併攏膝蓋。她戴著手套的兩隻手放在身子兩旁,擱在座椅上。
「到了。」他忽然說。計程車停靠在一條美麗的林蔭大道上的梧桐樹下,一間隱藏在院子與花園間的私人府邸前,有點像聖傑曼區常見的那種宅第。路燈在遠一點的地方,車裡還是一片陰暗,而且車子外頭正下著雨。
荷內說:「別動。一動都不要動。」他把手伸向她上衣的領子,解開領結,然後解開紐扣。她略微往前傾身垂胸,以為他要撫摸她的胸部。不是。他只是摸索著胸罩的吊帶,用小刀割斷,取下胸罩,再扣好她上衣的紐扣。她現在胸部光溜溜的,不受拘束,就和她的腰部、腹部,一直到光溜溜的膝上一樣不受拘束。
「聽著,」他說。「現在,妳已經準備好了。妳走吧。下車,去按門鈴。跟幫妳開門的人走。他怎麼吩咐妳,妳就照著做。要是妳不立刻進去,會有人來找妳。要是妳不立刻服從,會有人讓妳服從。妳的手提包?妳已經不需要手提包了。妳現在只是我提供給他們的女孩。沒錯,我也會在那裡。去吧。」
相同開場的另一個版本,相比之下較突如其來,也比較簡單:穿著同樣服裝的年輕女子被她的愛人與另一名不認識的朋友帶上了車。
車子是由不認識的朋友駕駛,愛人則坐在女人的旁邊,而這位不認識的友人對年輕女人解釋說,她的愛人負責讓她準備好,待會兒就要把她的手綁在背後,以及除了留著手套之外,他會幫她寬衣解帶,脫下她的絲襪,取下她的吊襪帶、她的內褲、胸罩,還要蒙起她的眼睛。
然後,她會被帶去城堡,那裡的人會根據她該做的來指示她。事實上,當她的衣物像這樣被剝除、雙手被綁起,車行半小時後,他們幫著她下了車,讓她登上幾階台階,然後穿過一、兩扇門。
過程中,她一直都蒙著眼,直到這時她是單獨一個人了,眼罩取了下來,發現自己正置身一間黑漆漆的房間裡。他們把她一個人丟在這裡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我不知道,總之有一世紀那麼長。
然後,門終於打開來,燈點亮了,我們可以看到她站在一間很尋常、很舒適,卻也有一點特別的房間裡等著: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但一件傢具也沒有,只有四周滿是櫃子。
開門的是兩個女人,兩個漂亮的年輕女人,打扮得像十八世紀的美麗侍女一樣:輕盈、蓬鬆的長裙直遮到腳,緊身胸衣讓她們乳房高聳,以束帶或扣子固定在胸前,蕾絲花邊環繞著胸脯,袖子是半長袖,眼皮和嘴唇都上了妝。她們都戴著緊緊圈著脖子的項圈,以及緊箍著手腕的手環。
我知道她們這時幫O解開了一直綁在身後的雙手,並跟她說她現在必須脫掉身上的衣服,接下來她們要幫她洗澡、化妝。
於是她們脫光她的衣服,收到旁邊的一個櫃子裡。她們沒讓她自己洗澡,還幫她洗頭、梳頭,就像在髮廊裡一樣,讓她坐在一張洗頭時可以後仰的椅子裡,等上好捲子、要吹乾頭髮的時候又可以把椅子豎直。
這過程需要至少一小時,但事實上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而且她就這樣一直赤裸裸地坐在這張椅子上。
她們還不准她交叉雙腿,也不准她併攏膝蓋。因為在她面前有一面大鏡子,占據了由下到上整個牆面,沒有任何東西遮擋,所以她只要看向鏡子,就會看見一覽無遺的自己。
當她準備好了,也化好妝了—眼皮微微搽上眼影,嘴唇塗得紅通通,乳頭和乳暈是粉紅色的,下體的唇瓣邊緣也呈紅色,腋窩和下體的毛髮都仔細地噴上了香水,股溝、乳房下的凹溝、手掌心也一樣—她們帶她來到一個擺著一片三面鏡、一邊牆上還有第四面鏡子的房間裡,好讓她把自己看得更清楚。
她們請她坐在房間中央的軟墊上等待,四面有鏡子環繞。軟墊上覆滿黑色的毛皮(有點扎著她的腿),地毯也是黑色的,牆面則是紅色的。她腳上穿著紅色室內拖鞋。
這個小房間的一面牆上有一扇大窗,窗外是一座陰暗的美麗花園。雨已經停了,風吹得樹木搖曳,月亮穿過高高的雲間。我不知道她在這件紅色小房間裡待了多久,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像她以為的那樣只有自己一個人,抑或有其他人正從牆面隱蔽的小洞裡窺探她的動靜。
但我知道,當那兩個女人再度出現的時候,其中一人手裡拿著布尺,另一人則拿著一個籃子,而且有個男人陪她們一起來。他身上穿著一件紫色長袍,袖口緊緊包著手腕,袖子連接肩膀的部分則非常蓬鬆,而且他的腰部以下,只要一走路,就會敞開來。他在長袍下穿著一件緊緊裹著大腿和小腿的緊身褲,但性器官的部位一無遮掩。
他一走進來,O最先看到他的性器官,然後看見他腰上插著一把皮鞭,再來是他頭上戴著連眼睛也覆住的黑色紗網罩,最後看見他也戴著黑手套,而且是小山羊皮製的。他叫她別動,並要另外那兩個女人動作快一點。拿著布尺的女人量起O的脖子和手腕。她的尺寸和大多數人沒兩樣,雖然有點偏小。
在另一個女人提的籃子裡,很容易找到適合她尺寸的項圈和手環。選中的項圈和手環是這樣的:好幾圈的皮革(每一層都很薄,厚度加起來不會超過一根指頭),用一種像鎖頭那樣的自動裝置,一按就上鎖,要用鑰匙才能打開。
在和鎖相對的另一邊,幾層皮革的中央有個金屬扣環;如果要用鐵鏈拴住她,可以從這裡穿過,因為手環與項圈已經緊縛著手腕與脖子,儘管不會緊到弄傷她,卻再無空間串入一條鏈子。
她們就這樣把手環和項圈戴到她的手腕和脖子上,然後那個男人叫她站起來,換他坐到她在軟墊上的位置,讓她靠近他的膝頭,把戴著手套的手伸進她的大腿間、摸她的胸部,對她說,今天晚上她單獨用過晚餐後,會把她介紹給大家。
她的確是自己一個人用餐,而且依舊是赤身露體。她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用晚餐,一隻看不見的手透過一個小窗口遞食物給她。最後,吃過晚餐後,那兩個女人又出現了。
她們帶她回到剛剛的小房間,一起將她兩手上的手環扣在她背後,再在她項圈的扣環繫上一件紅色大披風,披在她肩膀上,將她整個人包覆起來。不過,當她走路的時候,披風就會張開來,而她因為手被綁住而無法拉住披風。
一個女人走在她前面為她開門,另外一個女人走在後頭,隨手關上門。她們穿過一間前廳,走過兩間客廳,再進入一間圖書室,裡面有四個男人喝著咖啡。他們都穿著和剛剛第一個男人同樣的寬大長袍,只是頭上都沒有戴頭罩。
但O看不清他們的長相,看不出當中是否有她的愛人(他確實在其中),因為他們有人提著一盞燈,把燈光對著她照,讓她眼睛昏花。所有人動也不動,站在她兩側的女人是如此,在她身前看著她的男人也是。
然後,燈熄了,兩個女人離開了。不過,這時候有人又將O的眼睛蒙起來。有人要她往前走幾步。她略微蹭蹬,然後感覺到自己正站在火爐前,而那四個男人就是坐在附近:她感覺到熱氣,也在靜謐中聽到木頭微微爆裂的聲音。她面對著火爐。
一雙手掀起了她的披風,另一雙手在檢查手環是否確實扣緊後,順著腰部往下撫摸。這幾隻手都沒有戴手套,當中有隻手插入她前後兩個孔洞,動作粗暴,讓她不禁叫出聲。
有人笑了起來,另外有人說:「讓她轉過來,讓我們看看她的乳房和下身。」有人讓她轉過身子,爐火的熱氣襲上她的後腰部。有隻手抓住她一邊的乳房,有個嘴巴含住她另一隻乳房的乳頭,但她忽然失去平衡往後跌,幾隻手扶住了她。這時有人撐開她的腿,有人輕輕掰開她的唇瓣,她感覺有髮絲微微拂過她的大腿。
她聽見有人說要讓她跪下。他們照著做了。她的膝蓋很痛,尤其他們又不准她併攏膝蓋。她的兩隻手綁在背後,不禁令她身體前傾。這時候他們讓她往後仰,半坐在腳後跟上,就像修女的坐姿一樣。
「你從來沒把她綁起來過?」
「沒有,從來沒有。」
「也沒鞭打過?」
「沒有,但是正因為這樣……」答話的是她的愛人。
另一個聲音說:「沒錯。如果你綁過她幾次、打過她幾下,她會嘗到樂趣的,這樣可不行。得讓她跨過樂趣的門檻,嘗到痛苦的滋味,流下眼淚才行。」
有人讓O站起來,準備幫她解開束縛,但是是為了再把她綁在柱子或牆上。這時候,有人抗議說他要先佔有她,立刻就要—於是他們讓她再跪下,但這次是前胸靠在軟墊上,手依舊縛在背後,腰部高過胸部。
當中一個男人兩隻手抓住她的臀部,進入她裡面。之後他把位置讓給第二個人。第三個要從比較狹窄的那個孔洞進去,猛然地插入,令她叫喊出聲。他放開她後,她哼哼哀叫,眼淚沾溼了眼罩,身子滑落到地上。這時她感覺到有人的膝蓋湊近她臉旁。她的嘴巴也沒被放過,吸吮起性器官。
他們終於放開她,雙手被縛的她身上罩著大紅披風倒在壁爐前。她聽見有人在倒酒的聲音,他們喝了起來。她也聽到椅子移動的聲音。有人在壁爐裡添了柴火。突然,他們解開她的眼罩。
小桌上的一盞燈,還有壁爐裡的火—火勢又開始旺起來—微微照亮了這個牆面上排滿書的大房間。兩個男人站著抽菸。另外有個人坐著,膝蓋上放著一根馬鞭。而那個靠近她、愛撫她胸部的,是她的愛人。不過,四個男人都上過她了,她並沒有感覺她的愛人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他們跟她說明,只要她待在這座城堡裡,就會一直是這個樣子;她會看到強暴她或對她施與酷刑的人的臉,但這絕對不會發生在夜裡,而且她永遠不會知道誰該為最糟糕的事負責。他們鞭打她的時候也是一樣,除非他們要她看著自己被鞭打,才不讓她戴眼罩,但他們會戴起面罩,她就無從再分辨他們誰是誰。
她的愛人扶她站起來,讓她披著她的紅披風坐在壁爐邊的一把椅子上,聽他們要跟她說的話,看他們要讓她看的。她的雙手仍被束縛在背後。他們給她看一根馬鞭。鞭子是黑色的,又細又長,細細的竹條外包覆著皮革,就像在鞍具商的櫥窗裡看到的那種。
她最早看到的那個男人腰上插著的皮鞭很長,是用六條長長的帶狀皮革做成,尾端打一個結;另外還有一條繩子做的細鞭,尾端打了好幾個結,而且這條鞭子很僵直,就好像浸泡過水一樣。
它的確泡過水,就像她感覺到的,因為他們用這條鞭子滑過她的腹部,還掰開她的大腿,好讓她感覺到繩子碰觸她內側細嫩皮膚時是潮溼且冰冷的。
小桌上擺著鑰匙和鋼製的小鏈條。牆上有一面書櫃的內壁構成半面牆那麼高的凹廊,由兩根柱子支撐著兩邊,其中一根上頭釘了個鉤子,高度在一個人踮著腳尖、高舉手能碰觸到的地方。
她的愛人把O抱在懷中,一隻手在她的肩膀下,另一隻手搭在她私處,燒灼的感覺讓她就要撐不住。他們跟她說,待會兒要解開她的手,但只是為了用同一組手環加一條小鋼鏈把她拴到其中一根柱子上。
除了雙手被高高固定在頭上之外,她還能活動,也可以看到鞭子抽打過來。原則上,他們只會鞭笞她的臀部和大腿,也就是腰部到膝蓋以上,那個在帶她來的車子裡幫她打理好、讓她光著腿坐在後座的部位。
不過,在場這四個男人之一可能會想用短馬鞭抽她的大腿,好留下美麗的鞭痕,又長又深,又能久久留下痕跡。他們不會讓她一次承受所有的痛苦,而她可以盡情叫喊、掙扎、哭叫。他們會給她喘息的時間,不過當她一喘過氣來,他們又會重新開始。
他們不是以她的叫聲或眼淚來評斷成果,而是視鞭子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跡夠不夠深、夠不夠持久而定。他們提醒她,用這種方法來判斷鞭打有沒有效果,除了公正之外,除了讓被鞭打的人無法用誇張的呻吟來換取同情之外,他們還可以在出了城堡城牆外的地方、在戶外的公園中—就像經常會發生的那樣—或在任何一間普通公寓、旅館房間裡繼續鞭打她,只要事先用口銜封住她的嘴就好(他們立刻把口銜展示給她看);它只讓眼淚自由奔流,堵住所有叫喊,只縱容幾聲呻吟。但今天晚上,他們不打算封住她的嘴。相反的,他們想聽O喊叫,而且愈快愈好。
O出於自尊心而剋制自己不叫出聲,但撐不了多久就忍不住了。他們甚至還聽見她哀求他們放開她,哀求他們停一會兒。她為了躲過鞭子的鞭打,不停扭動身驅,幾乎在柱子前兜起圈子來,因為拴住她的鏈子很長,而且有點鬆,但很堅固就是了。
結果她的腹部、大腿前側和身體兩側,還有臀部,幾乎承受了一樣多的鞭子。在暫停一會兒後,他們決定在她腰間綁一根繩子,把另一頭綁到柱子上,再開始繼續鞭打她。為了讓她的身子好好固定在柱中央,他們把她幫得很緊,逼得她的上半身往一邊前傾,屁股往另一邊翹起。
從這時起,鞭子不再錯落,除非是故意的。考慮到她的愛人交出她的方式,O本來應該可以訴諸他的憐憫,但這麼做他反而會加倍殘酷對待她,好從她的嘴裡聽到他的權力是無可置疑的。
而且事實上,是他最先注意到皮鞭在呻吟著的她身上留下最少痕跡(用潮溼的繩鞭與短馬鞭則會立即留下痕跡),因此可以鞭久一點,而且幾乎可以想打時就打,於是他請他們改而只用皮鞭。
在這之間,他們當中有人只愛女人和男人共通擁有的後庭,被她高高翹起的屁股所吸引,而她愈想要逃開,就愈是挑逗人,於是他要求眾人暫緩一下,讓他好生消受一番。
他掰開她被鞭子打得仍熱燙燙的臀部,不無困難地插入她,還一邊表示得讓這個孔洞更方便插入。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可行的,也會找方法擴大她的後庭。
他們終於解開這個年輕女子。披著紅色披風的她,腳步蹣跚,幾欲昏倒。在帶她回到她的牢房前,他們告訴她在城堡裡必須遵守的相關細節,以及她離開城堡後(離開以後她也不得自由)必須繼續遵守的規矩。
他們讓她坐在靠近壁爐邊的一張椅子上,然後按了鈴。之前接待她的那兩名年輕女子,帶來她停留這裡的期間該穿的服裝,以及一隻戒指,讓在她之前來過城堡或在她離開後來到城堡的客人們可以藉此認得她的身份。
這身服裝和她們的很類似:帶撐架的馬甲在腰際緊緊束攏,上漿的襯裙上搭了一件裙身寬大的連身裙,短上衣包裹的乳房呼之欲出;那副馬甲讓乳房高高聳起,蕾絲花邊幾乎遮不住它;襯裙是白色的,馬甲和連身裙則是水綠色的綢緞,搭配白色的蕾絲花邊。
穿好衣服後,O又回到壁爐邊的椅子上。暗淡的服裝,將她的臉色襯得更蒼白。兩個年輕女人什麼話也沒說就要走了。四個男人之一在她們經過身邊時攔下其中一位,比手勢要另一個女人等一下,然後帶著他攔下的那個女人回到O的身邊。
他讓女人轉過身,一隻手抓住她的腰,另一隻手掀開她的裙子,展示給O看,並說明為什麼要她們穿這樣的服裝,以及這種設計多麼具有巧思,只要加上一條簡單的腰帶,就能隨意把裙子高高掀起,方便他們取用裙下的一切。
事實上,他們常讓女人在城堡或園子裡用這種方式四處走動,或只是撩起裙子前面的部分,而且不管前後都一樣撩到腰際。
他們讓這個年輕女人展示給O看怎麼挽起裙子:捲起好幾捲(就像把頭髮捲進髮捲那樣),再用腰帶緊緊繫住,前面就捲在正中央,好讓下腹露出來,後面則捲在後背正中央,露出臀部;不論從前面或後面捲,襯裙和裙子都在兩側像瀑布一樣往下垂墜。而這個年輕女人就和O一樣,臀部有短馬鞭的鞭痕。
展示完後,女人離開了。他們對O說了下面這段話:
妳在這裡是為了服侍主子們。白天,會讓妳做一堆家事,像是掃地、收拾書架上的書或插花,又或者是伺候主子們吃飯。不會有比這些事更困難的事。
不過,只要命令一下達,或只要稍有指示,妳就要立刻照做,因為妳真正的工作,是交出妳自己。妳的手不是妳的,妳的胸部,妳身上的孔洞,都不是妳的;只要我們高興插入,就可以盡情地進出。還有一件事,妳心裡要時時記住的是,妳沒有權利逃開或閃躲。
在我們面前,妳的唇永遠不會完全閉合,也不準交叉雙腿,或把腿併攏起來(從妳一到這裡,妳就知道自己沒有權利這麼做)。這對妳和我們都意味著,妳的嘴、妳的肚腹和妳的腰臀,全都為我們而敞開。
在我們面前,妳永遠不準碰自己的乳房:那一對馬甲高高托起的乳房,是屬於我們的。在白天,妳會穿著衣服,如果我們命令妳掀起裙子,妳就要乖乖掀起,而且誰想享用它就能享用,不戴面罩—除了他想鞭打妳的時候。
日落以後、日出以前,妳不會被鞭打。但除了那些可以隨意鞭打妳的人賞妳鞭刑之外,如果妳白天沒有遵守規定—意思是,要是妳沒有樂意聽命,或是抬眼看了跟妳說話或佔有妳的人—晚上妳就會被鞭打處分。
妳永遠不能看我們的臉。當我們在晚上穿的服裝裡露出我們的性器官,像妳現在眼前看到的,這不是為了方便,因為不穿這身服裝也同樣方便,而是出於傲慢無禮,要讓妳的眼睛盯住它看,不看別的地方,讓妳知道妳的主子就是它,妳的唇第一要務是為它所用。
白天裡,我們穿著一般的服裝,妳則穿著現在這身衣服,也要遵守同樣的命令;要是我們命令妳敞開妳的服裝,等我們佔有完妳以後,妳要自己穿好衣服。而在夜裡,妳只會有妳的唇和被掰開的臀部來尊崇我們,因為妳的手會被綁在身後,而且會像妳剛才被帶來時一樣全身赤裸。
我們如果蒙起妳的眼,是為了惡待你和鞭笞你—現在妳已經知道我們會怎麼打妳了。這麼說來,妳應該要習慣接受鞭打,因為只要妳在這裡,每天都會受到鞭打,但這不是為了我們的樂趣,而是為了妳的教育。
妳會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如果晚上沒人想要妳,妳得等著負責鞭打你的僕役到妳孤單的牢房來施用妳該接受而我們沒有興致給的。
事實上,鞭打妳和把妳鍊起來—拴在妳項圈的扣環上,讓妳感覺稍微有點緊地綁在床頭,一天好幾個小時—都不是為了讓妳感覺痛苦、讓妳叫喊,或是流眼淚,而是要讓妳感覺到妳不是自由的,讓妳知道妳完全受控於妳身外的事物。
等妳離開這裡後,妳會戴上一枚戒指,好讓人分辨出妳的身份。到時候,你會知道妳應該服從戴著同樣標誌的人—即使妳身上穿著再平常不過的服裝,他們也會知道妳在裙子底下永遠都是赤裸的,而且是為了他們而赤裸。要是有人覺得妳不聽話,就會再把妳帶回這裡,我們會帶妳到妳的牢房去。
在他們對O說話的時候,剛剛那兩個幫她穿衣服的女人又回來了,站在剛剛他們鞭打她的柱子兩邊。不過,她們沒有碰到柱子,彷彿它讓她們感到害怕,或是他們不准她們碰觸到它一樣(比較可能是這個緣故)。
男人說完話後,她們走到O的旁邊。O知道自己應該起身跟她們走,於是她站起身,兩手拎起裙子以免踩到而跌倒,因為她不習慣穿長裙,而且覺得穿著這麼厚底、高跟的鞋子走路不太穩。
這雙鞋上有一條和她的衣服同樣是水綠色的厚綢緞帶,防止鞋子從腳上鬆脫。在彎下身時,她轉過頭。兩個女人正等著她,但那四個男人已經不看她了。她的愛人席地而坐,背靠著軟墊,弓起膝蓋,兩邊手肘頂在上頭,手裡把玩著皮鞭。
她剛跨出第一步要走到那兩個女人身邊時,她的裙子拂過他。他抬起頭,對她微笑,叫她的名字,然後站起身。他輕撫著她的頭髮,用指尖順了順她的眉毛,柔柔地吻著她的唇。他大聲對她說,他愛她。
O顫抖著,畏懼中發現自己對他說出「我愛你」,而且是真心的。他將她攬進懷中,對她說:「我親愛的,我心所愛。」他吻她的脖子與耳腮邊,她把頭靠到他紫色的袍子上。
然後他推開她,示意那兩個女人讓開,讓他可以背靠著小桌子邊。他很高大,桌子卻沒很高,他穿著紫色緊身褲的兩腳微屈,身上的袍子像帳子一樣展開來,小桌邊上的突飾微微托起他沈重的性器官與周圍的淺色毛髮。
另外三個男人走近過來。O跪在地毯上,綠色的洋裝有如花冠一般在她四周綻開。她的馬甲緊緊箍著她,乳房在靠近她愛人膝蓋的地方。有個男人說:「燈再亮一點。」他們調整燈光,讓光源直接投射在他的性器官和她的臉上。她的臉離他的性器官很近,而她的手愛撫著它。
這時候,荷內突然命令道:「再說一遍我愛你。」於是O說了:「我愛你。」輕盈得就像她的嘴唇小心翼翼地觸碰他還被保護在柔軟皮膚下的性器官前端。
正在抽菸的另外三個男人評論著她的動作、她的嘴在他的性器官上的閉合、上上下下滑動,以及她因為它直撞入她的喉嚨、頂住她的舌頭而忍不住作嘔出聲,臉上因此滿是眼淚,卻仍在被硬起來的性器官塞滿嘴時,口中喃喃說著:「我愛你。」
那兩個女人分別站在荷內的左、右側,讓他兩手分別環繞在她們的肩頭。O聽見其他三個男人的評論,努力在這些話語之外傾聽她愛人的呻吟。她專心一意,以無比的敬意,以她知道他會喜歡的緩慢速度來撫愛他。
O知道她的嘴巴長得很漂亮,因為她的愛人願意深深刺入他的性器官,因為他願意在別人面前接受吸吮,因為他最後終於噴發出來。她對待她愛人的方式,就像對待一個神祇。她聽見他叫喊出聲,聽見其他人的笑聲,她接收了一切後,身子癱軟倒地。兩個女人扶她站了起來。這一次,她們帶走了她。